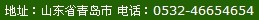|
元缂丝大威德金刚曼陀罗约-年缂丝本体纵.5横厘米,连装裱、镜框厚9.5厘米,重.5千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一)缂丝和唐卡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元代佚名作品缂丝大威德金刚曼陀罗,是目前尺寸最大的元代缂丝作品(纵.5横厘米),又是唯一带有帝后供养像、唯一有题记、也可以通过供养人形象和题记确认其宫廷艺术性质的缂丝,也是唯一可以明确纪年的元代缂丝。它从年入藏大都会博物馆以来即引起学界重视。它与元明宗、元文宗兄弟之间的皇位之争存在密切关系,也已成为共识。但是由于能够亲睹原作的国内学者不多,它在国内的介绍与研究还不够充分;关于它的产生背景和生产工艺,还存在争议和未解之处。缂丝又作“克丝”“刻丝”“刻色”,是一种传统丝织工艺,工艺特征是“通经断纬”,或称“挑经显纬”,即在贯通的经线上,以小梭织纬,通过颜色不断变化的纬线来构成图案,在不需要图像呈色的地方,则于背面割断纬线,以减轻重量。因此它的效果正面华丽而背面褴褛,只能供张挂观赏。缂丝起源于汉代西域印欧裔居民的缂毛工艺,现在发现的最早实物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公元7世纪)。大都会博物馆特展图录《丝贵如金——中亚和中国的丝织品》中指出,散居的回鹘部族对缂丝的应用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唐朝、辽、北宋、西夏和元代缂丝工艺都受到过他们的影响。唐朝的缂丝工艺还比较简单,到北宋成熟,并在北宋晚期从装饰艺术提升为欣赏性艺术品,用于仿制山水、花鸟、人物画,亦用于装裱和包首。这一技术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件缂丝属于藏传佛教卷轴画(唐卡),可以体现元代宗教艺术中独具特色的一个方面。现代藏传佛教卷轴画按材质和工艺分成丝绢唐卡(“国唐”,工艺包括织、绣、贴、印)和绘画唐卡(“止唐”,本地包括布本、绢本、纸本,工艺除手绘外,也包括版印)。缂丝应用于唐卡,是“国唐”的一种,因其昂贵,产量和存世量都很少。最早的实物是在宁夏黑水城出土的一些唐卡及其残片,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它们的年代通常被认为属于西夏(古代党项人以宁夏为中心地域建立的王国,-年),西夏是藏传佛教向内地传播的重要桥梁;但是也有可能属于元代,因为黑水城在元代仍然是西北重要城市。如果西夏已经开始生产缂丝唐卡,那么很可能是受到了散居甘肃的回鹘人的影响。 元代缂丝兼融并蓄了回鹘人、西夏人和南宋人的生产工艺。在元廷主持缂丝织造的官员唐仁祖就是一名回鹘人。但是元代的大型坛城唐卡——本文采用它在西方更常用的名称“曼陀罗”,尺寸和重量都达到惊人的程度(如本件“大威德金刚曼陀罗”的长宽都超过两米,重逾千克),就不仅吸收了来自宋朝的织绣如绘画传统,也吸收了来自中亚和西亚的挂毯图像艺术传统(中国织毯艺术自汉唐以来也有悠久的传统,但其图像是图案而非绘画,与元代出现的大型厚重缂丝有很大的差别)。 藏传佛教早期缂丝唐卡存世作品很少,除少量收藏在宫廷中(经元、明、清宫廷递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赐给西藏上层僧侣(现藏于拉萨布达拉宫),也有部分散见于西方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布达拉宫已知有三件13世纪初年的西夏缂丝唐卡(早于蒙古帝国征服西夏),分别为不动明王唐卡、除障明王唐卡,以及西夏末期或元代的贡唐喇嘛相唐卡;台北故宫博物院已知有两件元代缂丝唐卡,分别为文殊菩萨唐卡和喜金刚唐卡。不过,学界对这些唐卡的年代仍然存在争议,归属意见分布于西夏到元代之间。 缂丝唐卡中的曼陀罗尺幅较大、精像精密,传世量更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元代缂丝曼陀罗,除了本件大威德金刚曼陀罗,还有一件须弥山缂丝曼陀罗,在内容、纹饰和画风上呈现出更强烈的汉化特征,色调清新雅致,山石造型尤其是青绿设色接近元初画家钱选的风格,年代可能晚至元代中后期(14世纪初期到前半期);织法细密,后背断缕平整,接近南宋工艺,其产地可以确定是在南方。 元缂丝须弥山曼陀罗14世纪缂丝纵94.6横96.5厘米,厚6厘米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宽到绘画曼陀罗,会发现国外学者将流行于西藏的曼陀罗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2-14世纪的“噶玛巴风格”(TheKadampaStyle,即噶当派)时期,14-16世纪的“萨迦风格”(SakyapaStyle,即萨迦派)时期,以及17-19世纪的格鲁派统治阶时期(达赖喇嘛时期)。 类似于大都会大威德金刚曼陀罗那样复杂构图的坛城曼陀罗绘画较早实例见于12世纪的噶当派风格,如12世纪所绘的胜乐金刚(Samvara)曼陀罗,画法上还带有近似于古格白庙和红庙部分壁画的涂绘风格,较为粗犷。 这种坛城构成,到萨迦风格中更为流行,并进一步精致化。如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另有一件绘画无我佛母曼陀罗(馆藏号.4)被馆方定为约年,形式精美严密,但是图像组成较大都会大威德金刚曼陀罗略为简单,尺寸也较小(纵82.50横72.40厘米);14世纪晚期制作于西藏的金刚界(Vajradhatu)曼陀罗已经极度精致严密,15世纪所绘的大威德金刚曼陀罗的细密程度虽不及前述金刚界曼陀罗,但在构图上与大都会大威德金刚曼陀罗有更多共通之处,可以呈现大威德金刚曼陀罗自身的图像特征,其流行区域也扩展到尼泊尔。它们都拥有接近正方的形制,主尊居于画面正中,周围环绕以复杂的图像,上下两边缘有分块或成列的小图像,除了主尊以较小体量多次出现,还表现大德高僧、供养人、天女、护法等。 西藏中部地区胜乐金刚曼陀罗12世纪布本重彩尺寸不详印度J.P.Goenka收藏 元无我佛母曼陀罗约年布本重彩,金彩和墨纵82.5横72.4厘米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西藏地区金刚界曼陀罗14世纪晚期布本重彩纵84横73厘米海外私人收藏 西藏中部地区大威德金刚曼陀罗15世纪布本重彩纵52横41.9厘米海外私人收藏 尼泊尔财续佛母曼陀罗年布本重彩纵.50横87.63厘米海外私人收藏 尼泊尔曼陀罗15世纪晚期布本重彩纵40.6横35.5厘米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到格鲁派时期还出现了以多个这样的坛城曼陀罗为单位,组合而成的更大的曼陀罗。 总体上看,这些大型曼陀罗的构图方式、人物造型方式和线条、设色等方面的形式特征,都具有较强的延续性,13世纪的噶举风格到14世纪萨迦风格的沿续尤其明显,要作细致分期是比较困难的。作品断代的依据,除了设定形式与仪轨由简单粗犷向复杂精美乃至繁复进化这个前提之外,往往还要依据收藏传承、伴随出土物等旁证来解决,或者根据画面人物身份或风格特征推测出来。大都会大威德金刚曼陀罗虽然因供养人题记而有了较为明确的年代归属,被视为缂丝曼陀罗这个品类中唯一可以明确断代的作品。不过它的年代(14世纪前半期)在现存缂丝作品中也是较晚的,对缂丝曼陀罗和绘画曼陀罗所起的年代标尺作用还有很大局限性。 (二)大威德金刚坛城和帝后供养人 大威德金刚梵名称“阎魔德迦”(Yamantaka),形象是牛头人身、多臂多腿,因此又称“牛头明王”;英文中更常用的名称、来自梵文发音的Vajrabhairava则是其别称“怖畏金刚”。它的功能是降恶护善,在清代占统治地位的格鲁派中是五大本尊之一,在元代萨迦派里也有很高的地位。它是由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帝师八思巴的弟子沙哕巴(JiningShaluobaguanzhao)从西藏介绍进内地的,为皇室所尊崇。 大威德金刚曼陀罗各部分内容分布编号示意图 这件曼陀罗构图宏伟精密,图像学构成复杂。大都会博物馆展出此幅曼陀罗的展厅里的图像结构和内容说明,按位置和内容将画面分为14个部分或类别(李丹丽[DeniseLeidy]编),这里结合《丝贵如金》一书中GennadyLeonov所编的内容讲解,译介如下: 1大威德金刚,九头,正面三眼,三十四臂,十六条腿,本坛城主尊,修习的力量源泉。 2大威德金刚的随从——阎摩护法。主尊外围的四个中号阎魔护法像朝向四方,它们之间夹着四个小号像;坛城四门之间的外墙用金刚杵和垂珠为篱,内墙有小号阎魔护法像的阵列,每边八个,加上四角,一共是三十六个;曼陀罗左下角的区域里,空行母顶上还有一个小号的阎魔护法像;曼陀罗最下面的一横列形象,除了左右下角的四位帝后供养像,中间则有六个中号的阎魔护法变体像,双臂双腿,拥抱配偶,皮肤呈现不同的颜色,不同于主尊的深青色,并踩在白色水牛背上,最右边是一个青色的阎魔护法单身像,它们的左边则是一个青色的麻曷噶剌(?)。 3一圈骷髅(藏传佛教称为嘎巴拉),象征大威德金刚挑战死亡的力量;这构成了坛城的内圈。 4坛城(有四门的方形宫殿),四个门楼为印度教式建筑,门洞两侧有两头脸朝外的公羊拱卫,门楼外则有两头脸朝外的异兽拱卫,它们长着羊角和象鼻,嘴里喷出的泉水连接形成了门楼上方的拱门;每个门里有一个小号的阎魔护法像守卫。 5在坛城的四个门楼两侧,带有中亚风格的唐草底纹上,分布着八个灌顶瓶,装有净水及草药,为灌顶仪式中所用;这与坛城四门小号大威德金刚像阵列和内圈骷髅之间的四角空间中所画的卷草番莲底纹上的八个灌顶瓶,形成了呼应。 6一圈山形的莲花瓣(莲花山),象征重生和纯净;这构成了坛城的中圈。 7八大寒林(墓地),每个寒林图像单元中都包含一个佛向弟子传法的场景,也包含阎魔护法、蛇神、悉堵坡(佛塔)等形象,可能也包含来自地下世界的饿鬼形象;每个图像单元的中部则是印度教的神——骑鹅的梵天,骑象的因陀罗,骑海兽摩伽罗(makara)的水神伐楼那,骑鹿的风神伐由(Vayu)。通常八大寒林拥有八个印度教神,但在这幅曼陀罗中有九个——顶部那个单元中有两个。八大寒林外圈以金刚杵环绕,象征修行者通过曼陀罗,在追求与主尊合一的隐喻性的旅途中的净化需求。 8一圈火焰纹,以高度装饰化的手法表现,象征毁灭和纯净;这构成了坛城的外圈。从火焰的烧炼,到八大寒林的修行,再到莲花山的纯净,象征圈外的修习者在接近主尊所居的坛城过程中层层净化。 9四个主要的神,都出于大威德金刚法统,在此作为护法。它们都被表现为踩在白色水牛背上: 9a四臂的麻曷噶剌,抱着他的配偶(恰杜尔普迦,Chaturbhuja) 9b六臂的麻曷噶剌(Shabhuja) 9c有牛头和兽皮肤的阎魔护法 9d红色怒尊(怒尊甘露旋) 10大成就者(mahasiddha),或许是大瑜伽士萨惹哈(Saraha),持箭。 11一众空行母,是力量的象征,但在这里的作用更像供养天女,以手持的供物或自身的舞乐供养护法主神。 12顶部一横列显示这件特别的曼陀罗的修习法统: 12a本初佛(金刚总持) 12b护法神达摩波罗(dharmapala,可能是麻曷噶剌的一种化身) 12c大成就者毗鲁巴(Virupa,又作毗瓦巴Birvapa);他出现在这件曼陀罗中的原因是他曾被其师龙智(Nagabodhi)邀请参加大威德金刚的祭仪。 12d戴红帽的僧人,表示这件曼陀罗是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红帽系”)信徒制作的,他的身份可能是下列三者之一:萨迦派创始人昆·贡却杰布宝王(4-),其子、萨迦派初祖贡噶宁布(-),以及萨迦派五祖、元世祖时期的帝师八思巴(-);其后向右排列的另外十位无帽僧人像,应该是按世系排列的萨迦派上师。这一列僧人形象排列在毗鲁巴之后,应该是象征着他们传承了毗鲁巴的大手印(Mahamudra)。 13麻曷噶剌 14供养人像: 14a和世王束(音剌),图帖睦耳的长兄,即位为元明宗,年在位 14b图帖睦耳,忽必烈的玄孙,即位为元文宗,-年在位 14c卜答失里,图帖睦耳之妻 14d八不沙,和世王束之妻 大威德金刚曼陀罗的左右下角是两位皇帝和两位皇后的供养像,分别带有藏文题记(原来可能还有汉文题记,已脱落),据藏文题记,左下角两位男子分别意为“图帖睦耳皇帝”和“和世王束皇子”,即元文宗和元明宗,右下角两位女子分别意为“卜答失里皇后”和“八不沙皇后”,分别为元文宗和元明宗的皇后。由此可以判断这件曼陀罗制作的准确年代。 大威德金刚曼陀罗左下角元文宗(左)和元明宗(右)供养像 大威德金刚曼陀罗右下角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左)与元明宗皇后八不沙(右)供养像 按《元史》中的文宗和明宗本纪记载,他们皆为武宗海山之子。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也孙铁木耳崩,丞相权倒剌沙未迅即立太子阿速吉八为帝,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权臣燕铁木儿伺机在大都(今北京)发动政变,谋立武宗子为帝;而武宗长子和世王束当时远在漠北,燕铁木儿为抢占先机,至建康(今南京)迎其弟图帖睦耳,图帖睦耳于八月赶至大都,九月在大都即位(为元文宗,年号天历)。九月,泰定帝的太子阿速吉八则在倒剌沙拥立下即位于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双方爆发战争。十月,上都一方兵败,倒剌沙奉皇帝宝玺出降。文宗则屡次遣使迎请长兄。天历二年()正月,和世王束即位于和宁之北,为明宗,不改年号。四月,以皇弟图帖睦耳为皇太子。八月,明宗到达王忽察都(未建成的元中都),当年元武宗入京前曾在此停留观望,确认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控制了大都的局面,真心迎他入都即位,才大胆入都,并在即位后立弟弟为太子(即后来的元仁宗),兄终弟即,皆大欢喜。历史似乎要在中都重复兄弟温情的一幕。但是明宗在与文宗和诸王、群臣宴会后四天就“暴崩”,传为燕铁木儿毒杀,文宗至少是默许的。文宗随即复位,仍用天历年号,到至顺三年()去世。明宗皇后八不沙也于顺至元年()四月去世,据说是被卜答失里谋害。 《丝贵如金——中亚和中国的丝织品》中屈志仁等人的研究认为这件曼陀罗作于-年,即明宗死后、文宗第二次在位期,在年八不沙去世之前下令制作,年元文宗去世之后;在“年八不沙去世之前下令创作,完成于年元文宗去世之后。”《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中熊文彬则认为,带供养像的缂丝曼陀罗与皇帝即位关系十分密切,曼陀罗题记中称文宗为“皇帝”,明宗为“皇子”,可以证明它制作于文宗第一次登基而明宗尚未登基之时(-年之间);甚至可以精确到天历二年()八月之前,即文宗即位以后和明宗尚未即位之前。而在-年之间,曼陀罗中的四位供养人去世了三位,已经不适合再作为供养人出现。尚刚同意这个年代归属,但他提出一个重要意见,这件大型曼陀罗的织造需要耗费数年,因此更可能是利用泰定帝末期已经开始织造的曼陀罗,只是在最后织供养人时改成文宗兄弟,甚至存在抽换改织供养人面部的可能。 我们注意到,题记称两位女子皆为“皇后”,八不沙的“皇后”头衔不可能出现在在明宗登基前夕。文宗复位之初,八不沙还颇受文宗优容,天历二年八月,文宗“以钞万锭、币帛二千匹,供明宗后八不沙费用”,天历二年十一月,八不沙请求为明宗资冥福,命帝师率众僧作佛事七日,也命各处大观道士建醮。有可能就是在这次佛事中,八不沙要求制作了这件曼陀罗,将去世的明宗列为供养人。这时文宗皇后已立,但八不沙还被称为”后“。这似乎印证了曼陀罗上不能出现两个“皇帝”,但可以出现两个“皇后”。很可能将明宗改称“皇子”是出于文宗的授意,以强调自己在位的合法性,而八不沙只能被迫同意;并且明宗牌位置入太庙时在至顺元年()三月,曼陀罗题记中称他为“皇子”的理由很可能正是当时他尚未升祔。此外,我们也不可以汉人伦理观念的严格性来要求蒙古人,如元武宗和元明宗都曾以弟为第一顺位继承人,都不称为“皇太弟”而称“皇太子”,元顺帝即位初期将婶母卜答失里的尊号由皇太后升为太皇太后,汉臣“许有壬谏以为非礼,不从”。所以把元明宗称为“皇子”恐怕只是反映了元文宗主观上想将兄长退回到当皇子的状态,而不是明宗在那时还是皇子身份。因此也难以排除该件缂丝(或至少其中的帝后供养像)制作于文宗第二次登基之后的可能性。这件缂丝的制作时间,仍以大都会博物馆确定的-年最为合理。 (三)“织佛像”和“织御容” 这件缂丝曼陀罗属于“织佛像”,四尊帝后像是作为供养人出现的,但是具有肖像特点。将其中的文宗形象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元代帝后像册》中的文宗像对比,相貌显然同属一人。《元代帝后像册》被认为可能出于元中期宫廷画家李肖岩之手。因此这件曼陀罗上的供养像可以体现元代宫廷独有的“织御容”工艺。明宗肖像则不见于现存元代帝后像,仅见于此处。 大威德金刚曼陀罗左下角元文宗供养像 元佚名《元代帝后像册》中的元文宗像绢本设色纵61.5横4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织御容”最早记载的实例是阿尼哥在元世祖时“织锦为”“列圣御容”,世祖薨后又“追写世祖、顺圣二御容,织帧奉安于仁王万安之别殿”,他是“织御容”的创始人。《元代画塑记》总结说:“古之象物肖形者,以五采章施五色,曰绘、曰绣而已,其后始有范金埏土而加之彩饰焉。近代又有织丝以为象者,至于其功益精矣。” 阿尼哥(Anige,-)系尼泊尔王室后裔,自幼学习佛教和《佛说造像量度经》,擅长绘画和雕塑。据中文文献记载,元世祖中统元年(),年方十七岁的阿尼哥率领印度和尼泊尔选出的八十名工匠来到中国,参加建造萨迦寺金塔,一年后,金塔顺利完工,阿尼哥也被八思巴收为弟子,留在元朝为官,至元十年()任诸色人匠总管,后又兼领将作院事(将作院始置于至元三十年,),成为宫廷造型艺术的核心人物。 至于大都会大威德曼陀罗的主事官员,《丝贵如金》一书认为应是在英宗至治元年()起担任将作院使的明里董阿,这位明里董阿曾任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是元文宗第一次即位前亲自前往建康迎接他的重臣;他在天历元年九月(即元明宗死后)至天历二年四月还当了平章政事。《元代画塑记·御容》文宗天历二年二月、至顺元年八月两条记其名为明理董阿,官职皆为平章,可知他位居宰执至少近一年时间。更为吊诡的是,元顺帝(明宗长子)即位数年后羽翼已丰,于后至元六年()六月对文宗展开了报复,将文宗神位迁出太庙,将文宗皇后卜答失里流放至死,并下诏暴其叔婶之罪,其中有言文宗“当躬迓(明宗)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谋为不轨,使我皇考(即明宗)饮恨上宾。归而再御宸极”,并宣布将明里董阿“明正典刑”,可知明里董阿也是谋杀元明宗的参与者。那么,当年由明里董阿来主持织造这件大威德金刚唐卡(或者是在泰定帝时期的成品上加织或改织供养人形象)并将明宗的身份降为“皇子”,可以说是代替文宗本人出面,忠实地贯彻了文宗的旨意,也暴露了文宗君臣虚弱的内心。 两宋的缂丝工艺都可以再现细腻的绘画效果,但是并没有应用于肖像。“织御容”的需求因素潜藏在蒙古民族独特的宗教信仰中。12-13世纪(成吉思汗时代)蒙古游牧民在帐篷入口两侧悬挂毡或碎丝绸制作的神像,取其便携又不易损坏的特性,并相信这些神像会关心并保护他们全家,这就是萨满教的翁衮神像。以前死去的男女萨满(巫师)的灵魂,以及其他亡人的灵魂,均可成为翁衮,并不限于祖先。但是真正的萨满教仍然起源于对祖先的尊崇。从元世祖开始由阿尼哥制作织御容,显然受到宋朝帝后御容绘画的影响,但前无古人的织锦祖先像做法,则可以追溯到对蒙古毡制或丝绸制翁衮像及萨满教对祖先的尊崇。这是在萨满教的祖先翁衮神像和中原汉族王朝的祖先崇拜之间寻找到了最大的共性。而喇嘛教的神像除了用于引导修习,也能和萨满教的翁衮像找到共性,被蒙古贵族当成守护神像。当然蒙元统治者也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控的中亚、西亚和汉地的丝织力量,来满足对丝织品的迷恋。《元史·百官志》中记载的官作有两百余家,其中丝织及刺绣作坊最多,达72家。将奢侈的缂丝工艺用于皇家祖宗像,就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元代后期文宗和顺帝汉化程度很高,皇帝亲祀太庙的仪轨已经与汉族皇室无异,但皇室仍保留着许多“国俗旧礼”。御容用丝织,就是汉化外层包裹着的民族文化内核的显露。 对元代帝后及部分皇子“御容”、“御影”的记载见于《元代画塑记》,阿尼哥传记史料,《元史》中的仁宗、文宗、顺帝本纪等材料。这些敕命制作的帝后御容都是丞相、平章等高官督工执行,拨付大量贵重材料,不惜人力制成的。它们形式有绘、有织丝(应包括缂丝和织锦)。绘本制作只须数月,缂丝则长达数年,但是不能因此认为都是缂丝以绘本为底本。实际上,因为祖宗像需要反复制作,绘本和丝织本的图像关系应当是互为因借的。《元代画塑记·御容》类下记载的第一条史料是: 成宗皇帝大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敕丞相脱脱、平章秃坚帖木儿等,成宗皇帝、贞慈静懿皇后御影,依大天寿万宁寺内御容织之。南木罕太子及妃、晋王及妃,依帐殿内所画小影织之。将作院移文诸色总管府,绘画御容三轴,佛坛三轴。 其后所列“用物”皆为当是拨付与最后所列的“绘画”御容三轴和佛坛(即曼陀罗)。这里一共提到了三项制作:第一项,“织”帝后“御影”,依据是依供奉在万宁寺内的“御容”,后者可能是绘本,可能是织御容,或可能就是曼陀罗左右下角的供养像,绘、缂、织、绣皆有可能;第二项,为太子和晋王夫妇“织”像,依据是他们之前的“画小影”,供奉在帐殿内,应是中型画像;第三项,“绘画”御容三轴、佛坛(坛城,即曼陀罗)三轴,拨付了大批丝料、颜料和画框用料,三轴御容的依据很可能也是“大天寿万宁寺内御容”。 第二条史料记载: 仁宗皇帝延祐七年()二月十七日,敕平章帖木儿,道与阿僧哥、小杜二,选巧工及传神李肖岩,依世祖皇帝御容之制,画仁宗皇帝及庄懿慈圣皇后御容。其左右佛坛咸令画之。 这组帝后像及左右佛坛(曼陀罗)“各高九尺五寸、阔八尺”,与大都会大威德金刚曼陀罗颇为接近。不过尚刚指出《元代画塑记》里的“佛坛”都是画的,即绘画唐卡,而大都会缂丝大威德曼陀罗应为《元史》中记载的“织佛像”,其管辖部门“织佛像提举司,秩从五品”,地位不低。《元代画塑记》中的主要篇幅用于记载“佛像”类,不过绝大部分是雕铸塑,少量是绘画,未见有织物。 元代丝织工艺的两个中心是大都和杭州。《元代画塑记》没有提及诸色总管府(尚刚认为是纹锦局)的任务下派到哪里制作,但是宿白先生认为大都会大威德金刚曼陀罗的产地有可能是在杭州。据大都会博物馆的研究,这幅曼陀罗的背面露出的纬线断头留得较长,而且呈绞乱状态,也有在背面经线断后接续上另一根经线(有时会打结连缀)的情况,这些技术特征都接近于西夏而不同于两宋的精密工艺,并且与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的、产于南方的须弥山缂丝曼陀罗背面的细腻平整状态形成鲜明对比。这可以表明大威德金刚曼陀罗的工匠主力或主导来自西夏(或者回鹘)。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幅尺寸巨大的曼陀罗是分成数块织造的,再用彩色丝线织补在一起。分块织造的方法固然可能受限于缂丝机的幅面,客观上则便于运输,这说明它很有可能是在外地分块织就后运至大都缝合的。那么它的原始织造地是西夏故地吗?也不尽然。我们又注意到,一些皇冠和珠宝之类细节使用金箔覆盖在纸上,然后捻线并压扁后进行编织(大部分金箔已脱落,但仍可看到痕迹)。金线用于织物在中国也有悠久历史,应用于缂丝则始于元代,对金色的喜好同时满足了游牧民族和藏传佛教徒的审美偏好。不过尚刚先生根据朝鲜时期编纂的汉语教材《朴通事谚解》的记载分析指出,以金箔附丽于绵纸的纸金是汉族传统织金锦——金段(缎)子的特色工艺,而非分布在北方的西亚纳金锦——纳石失的特色。结合这些工艺特征可以认为,这件曼陀罗更可能织造于杭州,然后运至大都缝合,但是织造的人力却可能是以来自西夏(或者回鹘)的工匠为主力或主导。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端倪,却能令我们对元代南方丝织工艺中心的生产机制产生新的认识。 大威德金刚曼陀罗背面局部 大威德金刚曼陀罗背面局部 附:元文宗两次即位前后事件简表 时间 事件 文献出处 致和元年()七月 泰定帝也孙铁木耳崩。 (明)宋濂等:《元史》卷三十《泰定帝本纪二》,中华书局,年,页。 八月 权臣燕铁木儿在大都发动政变,谋立武宗子为帝,迎武宗次子图帖睦耳由建康至大都。 (明)宋濂等:《元史》卷三一《明宗本纪》,中华书局,年,第-页;卷三二《文宗本纪一》,第-页。 九月 天历元年() 丞相倒剌沙等拥立泰定帝皇太子阿速吉八于上都,改元天顺; 图帖睦耳即位于大都(为元文宗,年号天历);两都之战(上都阿速吉八对大都图帖睦耳)爆发。 (明)宋濂等:《元史》卷三十《泰定帝本纪二》,中华书局,年,页; (明)宋濂等:《元史》卷三一《明宗本纪》,中华书局,年,第页;卷三二《文宗本纪一》,第-页;《文宗本纪一》,第页。 十月 上都兵败,倒剌沙奉皇帝宝出降。 元文宗遣使迎长兄和世王束。 (明)宋濂等:《元史》卷三二《文宗本纪一》,中华书局,年,第页。 (明)宋濂等:《元史》卷三一《明宗本纪》,中华书局,年,第页。 天历二年()正月 和世王束即位于和宁之北,为明宗,仍用天历年号。 (明)宋濂等:《元史》卷三一《明宗本纪》,中华书局,年,第页。 四月 明宗以皇弟图帖睦耳为皇太子。 (明)宋濂等:《元史》卷三一《明宗本纪》,中华书局,年,第页;卷三三《文宗本纪二》,第页。 八月 明宗到达王忽察都,与太子(图帖睦耳)和诸王、群臣宴会后四日暴崩; 文宗复位,仍用天历年号; 文宗以钞万锭、币帛二千匹,供明宗后八不沙费用。 (明)宋濂等:《元史》卷三一《明宗本纪》,中华书局,年,第页;卷三三《文宗本纪二》,第页。 (明)宋濂等:《元史》卷三三《文宗本纪二》,中华书局,年,第-页。 (明)宋濂等:《元史》卷三三《文宗本纪二》,中华书局,年,第-页。 十一月 八不沙请为明宗资冥福,命帝师率众僧作佛事七日,亦命各处大观道士建醮。 (明)宋濂等:《元史》卷三三《文宗本纪二》,中华书局,年,第页;卷一一四《后妃传一·八不沙皇后》,第页。 至顺元年()三月 明宗祔于太庙。 (明)宋濂等:《元史》卷三一《明宗本纪》,中华书局,年,第页;卷三四《文宗本纪三》,第页。 四月 明宗皇后八不沙薨。 (明)宋濂等:《元史》卷三四《文宗本纪三》,中华书局,年,第页;卷一一四《后妃传一·八不沙皇后》,第页。。 十二月 文宗立长子阿忒纳答剌为皇太子(早夭,时间不详)。 (明)宋濂等:《元史》卷三四《文宗本纪三》,中华书局,年,第页。 至顺三年()八月 文宗崩于上都,遗命传位于明宗之子。 (明)宋濂等:《元史》卷三六《文宗本纪五》,中华书局,年,第页;卷三七《宁宗本纪》,第页。 十月 明宗次子懿璘质班即位于大都,为宁宗。 (明)宋濂等:《元史》卷三七《宁宗本纪》,中华书局,年,第页。 十一月 宁宗崩,年七岁。 (明)宋濂等:《元史》卷三七《宁宗本纪》,中华书局,年,第页。 至顺四年()六月 明宗长子妥欢帖木耳即位,为顺帝。卜答失里与大臣先已约以文宗次子燕帖古思(古纳答剌)为顺帝继承人。 (明)宋濂等:《元史》卷三八《顺帝本纪一》,中华书局,年,第页。 后至元六年()六月 顺帝将文宗神位迁出太庙,将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及其子燕帖古思流放至死,大臣明里董阿处死 (明)宋濂等:《元史》卷四十《顺帝本纪三》,中华书局,年,第-页;卷三六《文宗本纪五》,第页;卷一一四《后妃传一·文宗卜答失里皇后》,第页。 (致谢:本文撰写前期,笔者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担任高级访问学者,该件曼陀罗一直陈列在专门展厅,得以多次观瞻。感谢大都会同事李丹丽[DeniseLeidy]、史耀华[JosephScheier-Dolberg]慷慨提供研究资料,也感谢大都会教育部访问学者年度计划为笔者提供的研究机会,以及大都会WatsonLibraryAsianArtDepartmentLibrary提供的图书资料便利。国内学者尚刚、熊文彬对该件曼陀罗的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基础,亦在此谨此谢忱。) 本文作者: 邵彦(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罗中立谈《父亲》(油画)的创作感想 佳著推介:沈宁《闲话徐悲鸿》 中国绘画史研究之工具书(6):《中国鉴藏家印鉴大全》(上下册) 林木:集文院之长,舍戾行之短——阴澍雨写意花鸟之独特探索 免费下载:(宋)郑思肖撰《心史》(明崇祯十三年刻本) 免费下载:(明)陈洪绶《宝纶堂集》光绪戊子春会稽董氏取斯堂重刊本 首届全国画学文献学术研讨会征稿函 赞赏 长按北京看白癜风哪家医院疗效最好中科白癜风微信账号
|
当前位置: 金塔县 >邵彦元代宫廷缂丝唐卡巨制大都会博物
时间:2018/1/5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巴厘岛,穿越半个地球来睡服你
- 下一篇文章: 南昌生活亲爱的,五一我们去江西吧,我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