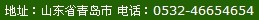|
漢代弱水中下游流域邊防系統中的“置” 郭偉濤(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北京) 中文提要:漢代張掖郡北部的肩水、居延都尉,其轄區就在弱水中下游流域。依託倉而建立、負責後勤供應的“置”機構,分佈於這一地區。如肩水都尉統轄的肩水、橐他、廣地三個候官駐地,及肩水城官(A35)等,均設立“置”。北部居延都尉轄區內,亦設立“置”,但多位於部隧。不同於懸泉置兼掌文書傳遞、供應招待等,弱水中下游流域邊防系統中的“置”基本上不負責文書傳遞,這一工作應由當地普遍設立的亭隧承擔。對著名的“甘露二年御史書”相關問題,及永田英正所開創的候官文書集成研究的方法,亦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思。 關鍵詞:置、弱水中下游流域、候官、置佐 劉邦稱帝不久,逃亡海島的田橫蒙詔前往雒陽覲見,途徑“尸鄉廄置”時自刎而死。[1]文帝即位第二年(前),因連續兩次日食而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要求“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2]史籍中關於此類“置”的記載不絕如縷,但言辭簡短,難以深考。 隨著懸泉置漢簡及其它敦煌漢簡的出土和零星刊布,張傳璽、何雙全、宮宅潔、張俊民、張德芳、趙岩、李並成、呂志峰等陸續展開對“置”的研究。[3]綜觀上述成果,基本上圍繞位於今敦煌市與瓜州縣交界處的懸泉置及其所出簡牘展開,而忽視了弱水中下游流域的“置”。[4]目前僅見吳昌廉、高榮兩位學者注意到北部居延地區的“置”,但亦未涉及南部肩水地區,[5]且將弱水中下游流域的“置”與懸泉置合在一起討論。如此處理,雖然在資料上可收左右逢源之效,但實際上未考慮到“置”的地域性特征。 筆者在閱讀居延舊簡、新簡及金關漢簡的過程中,[6]發現弱水中下游流域設立了“置”這個機構,通常被認為肩水候官所在地的A33遺址,設有“置”,橐他、廣地候官亦設“置”,肩水城官(A35)設立都倉置,北部居延地區亦設立“置”。而且,這一地區邊防系統中的“置”,其設置背景及功能,與處於郡縣民政體制下的懸泉置並不完全相同。 有鑒於此,本文先行考察這一地區“置”的具體分佈,在此基礎上揭示其設置的特點及職能。必須說明的是,弱水中下游流域不僅建置居延都尉、肩水都尉等軍事體系,亦有肩水縣、居延縣等民政機構,本文主要討論前者中的“置”。 一、肩水地區的“置”肩水都尉轄區內的“置”,筆者所見,似尚無學者討論及此。實際上,肩水、橐他、廣地各候官設有“置”,肩水城官所在地(A35遺址)設立都倉置。 (一)候官“置”在展開論證之前,有必要澄清“候官”的概念。嚴格意義上,塞候日常辦公處理政務的衙署,[7]才可稱為候官,其建築規模較亭隧更為宏大,通常包括被視為塞候居所的障,及附屬機構所居的塢院。而簡文常見的某某塞,如肩水塞,通常指肩水候統轄的整個防區。本文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候官”的概念。 證明肩水候官設立“置”的最直接材料,是下述這枚文書簡的開封記錄: 1.1、建始二年八月丙辰朔□□,北部候長光敢言之:□□廩鹽名籍一編,敢言之。.2A 鄭光私印置佐輔發 □□戊午候長鄭光以來君前.2B/A33 該簡形制為兩行,正面文字工整嚴謹,簡背筆跡與之不同,顯系文書送達後別筆所書。據簡文,建始二年(前31)八月北部候長光呈報廩鹽名籍,簡背印文“鄭光私印”及“□□戊午候長鄭光以來”顯示北部候長姓名為鄭光,文書由候長本人送來。該簡為呈文簡,當編排在廩鹽簿書末尾。建始二年九月無戊午,故簡文“戊午”當為八月三日,惜無法判斷該簿書是事先申請廩鹽,還是事後匯報廩鹽發放情況。[8]該簡出土地——A33遺址——在當時為肩水候駐地,而且文書一般逐級上呈或下發,故此該文書呈報對象當為肩水候。在西北邊塞文書中“君”一般指“候”,[9]開封記錄“置佐輔發君前”,顯示原簿書由名為輔的置佐在肩水候面前打開,亦與文書呈報對象吻合。最保守的推測,該簡涉及的建始二年八月三日,置佐輔在A33遺址。 無獨有偶,材料顯示橐他候官亦設有“置”,如下: 1.2、居攝元年……朔乙□,橐他候秉移肩水金關:□□ ……府官□73EJT23:A 置佐豐73EJT23:B 該簡右下殘,原文書字跡工整謹嚴,墨色較濃。文書發到金關後廢棄,刮削後用於習字,故正背兩面有些文字極潦草,墨色極淡。此處僅錄原來簡文,不錄後期習字內容。據簡文,居攝元年(6)某月橐他候秉移文肩水金關,或涉通關。簡背落款為“置佐豐”,顯示該文書當由名為“豐”的置佐負責。一般而言,橐他候發出的文書當由其駐地——橐他候官——的屬吏負責文書工作,因此該簡的“置”當設於橐他候官。此外,另有兩簡亦證明橐他置的存在: 1.3、橐他置佐昭武便處里審長妻大女至年卅五牛車一兩 建平二年家屬符子小女侯年四用牛四頭 子小男小奴年一歲73EJT37: 1.4、?……始二年九月甲辰,主官掾常付橐它置佐登EPT52:36 簡1.3為寬木牘,右側刻齒。該簡為橐他置佐審長的家屬符,詳載妻子、子女的身份名字年齡及車馬信息,通關時合符。簡1.4為單札,上端墨色脫去,部分文字無法釋讀。紀年僅存“始二年九月甲辰”,自昭帝至東漢早期,年號為“×始”且紀年至二年者,有本始、建始、永始、元始等,據曆日表,建始二年(前31)九月二十日、元始二年(公元2)九月二十六日的干支皆為甲辰。[10]而甲渠候官的“掾常”見於河平二年(前27)五月(.19/A8)和新莽天鳳元年(公元14年)六月(EPT5:50),雖然不能排除重名的可能性,但簡1.4主官掾常活動于建始河平年間的可能性更大一些,[11]故暫定該簡年代為建始二年九月二十日。這一天,主官掾常交給橐他置佐登某種物品,該簡或為錢物出入簿籍。兩簡明確顯示,成帝建始及哀帝建平年間,橐他置的建制是存在的。此前,吳昌廉曾據遮虜置與候官、橐他置與橐他候官同名的現象,推測“置”當與鄣相鄰或共構。[12]這一看法很敏銳,但理論上還存在另一種可能,即所謂“橐他置”是轄於橐他塞而非位於橐他候官的置,對外行文時往往亦稱為“橐他置”。不過,並無材料支持後一種可能。結合簡1.2置佐位於橐他候官的情況,兩簡所涉的橐他置很可能亦設於橐他候官。 廣地候官置與橐他情況類似,如下: 1.5、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癸亥朔癸亥,廣地守候紀移肩水金關:吏詣?官除如牒,書到出入,如律令。73EJF3:+A廣地候印十一月四日入置[13]輿商73EJF3:+B 1.6、府錄毋擅入常鄉廣地置佐鄭眾73EJT37: 1.7、□八人其一人車父·凡百卅九人軺車七兩□□□□牛車百一十两? □百卅人其十六人輸廣地置馬七匹牛百一十二其十五輸廣地置[14]? 73EJH1:30 簡1.5形制為寬木牘,字跡潦草。據簡文,因轄下吏卒出行,故廣地候移文金關。簡背具名“置輿商”,顯示該文書由商負責,商的身份為“置輿”。《漢書·嚴助傳》記載“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顏師古注曰“輿,主駕車者”,[15]據此“置輿商”即在“置”工作的駕車人。一般而言,駕車者地位低賤從事力役,應不負責文書工作,該簡可能為特例。[16]既然該文書由置輿負責,結合簡1.6、簡1.7,廣地候官亦當設有“置”的機構。另,該簡紀年為始建國二年(10)十一月癸亥朔癸亥,朔日與今人所推曆譜不符,[17]與73EJF3:相合,當以此為準。簡1.6為單札,墨色雖淡,字跡不似習書。原應為冊書,惜其餘不存。簡文難解,但“廣地置佐鄭眾”無疑應當連讀。簡1.7下殘,文字細密工整,分左右兩行書寫。據簡文,似當為某種車馬運輸統計簿,“其十六人輸廣地置”及“其十五(牛)輸廣地置”表示運送某種物資至廣地置。可惜的是,該廣地置與上舉橐他塞簡1.3、簡1.4類似,不知是設立於廣地候官,還是候官塞其它地方。比對肩水候官、橐他候官設立的“置”,廣地置似也應設立在廣地候官。 此外,另有殘簡顯示候官置的設立。如下: 1.8、?□義行候事移肩水金關:遣 ?□迎錢城倉。書到,出□如73EJT3:11A 置佐安73EJT3:11B 該簡形制為兩行,上端有燒灼痕跡,很可能該文書廢棄後即用作燃料。據簡文“義行候事”當發自某個候官,因轄下吏卒到城倉(A35)迎取錢物,故移書金關。簡背落款“置佐安”,顯示該文書由名叫安的置佐負責,故該“置”亦當設立於候官。惜不詳候官名稱。 據上,肩水、橐他、廣地三候官應當設立了“置”的機構。此外,肩水候官所在——A33遺址——亦出土不少相關文書,如下: 1.9、?陽朔二年六月乙巳佐博受居延張□?.11/A33 1.10、陽朔三年正月丁卯朔乙亥,置佐博敢言之:謹移糒粟麴.1/A33 簡1.9形制為單札,上下均殘,似為某種物資出入記錄,由佐博接收。簡1.10顯示,陽朔三年(前22)正月丁亥,置佐博上報某種簿籍,涉及糒粟麴等。有學者認為,河西邊塞文書中草稿多用單札,亦兼用兩行,而正本必用兩行,[18]據簡1.10形制為單札判斷,很可能為呈報文書的草稿。因此,該簡雖為呈文簡,並不證明由設於其它地方的“置”呈送過來,而應由設在A33遺址——也就是肩水候官——的“置”所起草。兩簡相距不足一年,前簡“佐博”與後簡“置佐博”當為同一人,只是文字省略而已。此外,A32遺址亦出土數枚相關簡牘,如下: 1.11、出黃梁米一斗一其□□建始三年三月丁未置佐親?73EJT37: 1.12、?□□□建平二年十一月丙戌置佐並受?73EJT37: 1.13、出麥十八石合□卩居攝元年六月癸未置佐玄付乘胡隧長放 73EJT23:+ 三簡形制皆為單札,均為物資出納記錄。簡1.11紀年為建始三年(前30)三月,此時肩水候尚駐A33,[19]該簡之所以出現在A32遺址,很可能因此時肩水候不在署,由A32遺址某個機構的官吏兼行候事,故此時設於A33遺址的“置”將文書呈給此地的兼行候事者。其餘兩簡紀年分別為建平二年(前5)十一月、居攝元年(7)六月,這兩個時間點,肩水候已經常駐A32遺址,不過,肩水塞的大本營——肩水候官——應該依然在A33遺址,推測“置”並未遷移,只不過相關文書轉呈至A32遺址了。 綜上,肩水候官所在地設立了“置”的機構,橐他、廣地候官亦如此。 (二)都倉置除設在候官的“置”外,肩水地區還設有所謂的都倉置。如下: 1.14、都倉置佐程譚葆屋蘭大昌里趙勤年卌八十二月癸亥北嗇夫豐出已入 73EJT37: 1.15、月十一日具記:都倉置牛車皆毋它,已北,尊以即日發去,有屬證居?者言:居延穀倉出入百十二石耳·祿得遣史蜚廉卿送卒□肩水,以今月二……屠李君及諸君,凡六人,車數十百兩,祿得吏民爲73EJF3:+ 簡1.14形制為單札,屬於通關出入名籍簡。細察圖版,末端“已入”兩字的位置偏右,與上面文字正中書寫迥然有別,顯系後期填注。若此不誤,則趙勤先出關后入關。就金關的具體方位而言,過關北行為出,南行為入,故此,都倉置當設於金關以南的某地。簡1.15左殘,簡首“月”明顯大於其它文字,故“月”或指當月。據簡文,似觻得派遣屠李等六人及數百輛車前往居延地區運輸穀物。書信開頭提及都倉置的牛車似已過關而北,寫信人“尊”亦已離開。因簡文殘缺,不清楚都倉置是否與觻得有關係,或許兩者並無統屬關係,僅因觻得運糧而臨時征調都倉置的牛車。 都倉置,顧名思義,當指設於都倉的置。明確都倉的位置,即找到都倉置的所在。據下簡,都倉似當設在A35遺址: 1.16、曹宣伏地叩頭白記:董房、馮孝卿坐前:萬年毋恙!頃者不相見於,宣身上部屬亭,迹候為事也,毋可憂者。迫駒執所辱,故不得詣二卿坐前。遣.14+.38+.43A 毋狀,願高賞卿到,自愛怒力加意,慎官事,叩頭幸甚。宣在驩喜隧,去都倉四十餘里,獨第六隧卒杜程、李侯常得奏都倉,二卿時時數寄記書,相問音聲,意中快也。實中兄.14+.38+.43B/A35 該書信原為寬木牘,裂為數塊,今三塊拼合,左側尚殘,文意不完。據簡文,曹宣寫信給董房、馮孝卿兩人,書信主要匯報曹宣自己服役的情況。其中“獨第六隧卒杜程、李侯常得奏都倉,二卿時時數寄記書”顯示,董房、馮孝卿兩人可能常託前往都倉的杜程、李侯將書信帶給曹宣,從這個表述看,董、封辦公地點當在都倉,而該簡出土自A35遺址,故即都倉所在。曹宣寫給董、封兩人的書信,送到了目的地。都倉之“都”字,原本即有總體、中心的意思,[20]該地築城,規模宏大,為肩水都尉轄區的中心,設在該地亦屬常理。另外,簡文“宣在驩喜隧,去都倉四十餘里”顯示,都倉與驩喜隧相距四十餘漢里,暫取42漢里,約為17.6公里。驩喜隧轄於東部,具體位置不詳,該書信涉及的第六隧當轄於左前部,在金關以北,[21]而東部候長駐地——A32遺址——距離A35遺址直線約9.5公里。[22]不過,漢代的里程一般為步行里數,並非直線距離。弱水沿線道路曲折回環,兩組數據相差近一倍,恐亦正常。驗以下簡,亦大致相符: 1.17、?□卿御至通遠,廿一日謁官,廿二日還,宿橋北,廿三日日迹,數……? ?迹南,日中迹北竟,還;廿六日旦迹南,日中迹北竟,還;廿七旦迹南,日……? ?□會吏□弩周初八日旦南迹,□日入,迹南竟,二日……? ?餔迹南竟;九日旦迹南,日中迹北至,還;五日旦迹南……?73EJD:A ?閒旦迹北竟還日食時入關將卒詣旦北至□□□旦迹? ?塞下餔南竟行莫宿都倉□召卒出入□□徙□□? ?稽落食陳卿舍日入到治所□宿趙□□? ?竟73EJD:B 該簡為寬木牘,上下皆殘。簡文似記錄了事主兩個月的主要工作,絕大多數為日跡。[23]正面未分欄,當豎讀,簡背分欄,每欄當從右自左讀,故此現存第三欄當讀為“日食時入關將卒詣行莫宿都倉”。若此不誤,則“日食時”入關,[24]暮宿都倉,正好為一日的行程。漢代軍隊輕行一日五十里,重行三十里,[25]該簡“將卒”而行,當可視為行軍,前進距離當在五十里左右。前引1.16顯示驩喜隧距都倉四十餘里,兩組數值差相仿佛。此外,還有不少簡涉及都倉,如74.17/A33、73EJT23:、73EJT23:、73EJT24:、73EJT37:、73EJT37:、73EJT37:、73EJH2:76、73EJF1:70及書信簡73EJT23:、73EJT30:27+T26:21、73EJF3:、73EJD:39等等,皆無助於考證都倉位置,不贅。 A35遺址因屬於肩水都尉駐地,故修築一定規模的城。這個城本身亦設專門機構進行管理,即城官,[26]亦稱肩水城官,長官為城尉。換言之,城尉與肩水都尉同駐A35遺址。材料顯示,肩水城官承擔了供應肩水都尉轄區內吏卒口糧廩食的任務。如下: 1.18、·西部河平四年五月吏卒稟城官名籍72EJC: 1.19、·初元五年六月所受城官穀簿.3/A32 1.20、永始四年七月壬寅朔? 廩城官名籍一編,敢?73EJT24: 1.21、石南亭卒朱護就食城官73EJF3: 1.22、建始元年三月甲子朔癸未,右後士吏雲敢言之:迺十二月甲辰受遣,盡甲子,積廿日,食未得。唯官移.1/A33 城官致,敢言之。以檄報:吏殘日食皆常詣官廩, 非得廩城官。.4A 董雲令史博發 三月丙戌肩水庫嗇夫魚宗以來君前.4B/A33 上舉六枚簡皆涉及城官。前兩簡形制皆為單札。簡1.18為肩水候官塞所轄西部塞製作的吏卒廩城官名籍簿書的標題簡,簡1.19為某機構接受城官穀物簿籍的標題簡。簡1.20為兩行,據簡文,為某機構上呈廩食城官名籍簿書的呈文簡,或為某部呈送,該簡當置於原簿書最末。簡1.21形制為單札,似為某種戍卒廩食簿籍冊書的一枚。石南亭轄於橐他塞,[27]因亭卒前往城官就食,該簡可能屬於通關致書的附牒。簡1.22是一份冊書,兩簡形制皆為兩行,均出土自A33遺址,編號相近。後簡正面文字“城官致敢言之”筆跡書風與前簡相似,工整謹嚴疏密有致。兩簡所記內容為同一件事,“唯官移城官致”語句相接,後簡背面董雲與前簡右後部士吏雲同名。綜合判斷,兩簡可復原成冊。據簡文,右後部士吏雲向肩水候官呈文,請求移文城官補足二十日的廩食。簡背右上角“董雲”當為原封之印的名字,當即右後部士吏雲。“三月丙戌肩水庫嗇夫宋宗以來”顯示該文書由庫嗇夫宋宗帶到肩水候官(A33),而右後部在肩水塞南端,因此肩水庫當與士吏董雲治所相近,可能順路帶來。“令史博發君前”顯示,文書由令史博在肩水候面前開封。正面小字“以檄報吏:殘日食皆常詣官廩,非得廩城官”當為肩水候官的批復。尚不清楚,這一批復是候官立即做出,還是請示肩水城官後做出。上舉諸簡,皆顯示城官承擔供應亭塞吏卒穀物廩食方面的功能。而且,據末簡推測,很可能城官作為總的後勤基地,平時將穀物運送至各候官,由候官再行分配發放,並非直接由城官向全體吏卒發放,遇到特殊情況才由城官臨時發放。若此不誤,則城官必設有規模不小的倉,專門存儲穀物,而A35遺址臨近騂馬屯田區,該地亦出土不少屯田相關的簡牘,結合都倉的大致方位判斷,都倉設在A35遺址亦合情合理。 此外,肩水城官恰恰設有“置”,如下: 1.23、始建國三年五月庚寅朔壬辰,肩水守城尉萌移肩水金關:吏所葆名如牒,書到出入,如律令。73EJF3:A 置輿鳳73EJF3:B 該簡形制為兩行,字跡工整。據簡文,始建國三年五月肩水守城尉萌移文金關,涉及人員通關。簡背具名“置輿鳳”,比對前引簡1.5可知,在“置”駕車的鳳負責肩水城尉發出的這份文書。據此,肩水城官當設有“置”。都倉既設在該地,那麼該簡的“置”當即都倉置。需要強調的是,雖然都倉置亦設在A35遺址,但該機構應該直屬於肩水城官,而非肩水都尉府。 此外,A35遺址不僅設都倉,亦設庫。如下: 1.24、建平二年八月乙卯朔辛酉,肩水庫嗇夫賞以小官印行城尉事,移肩水金關: ?73EJT37: 1.25、始建國二年八月甲午朔丙辰,肩水庫有秩良以小官印行城尉文書事,移肩水金關、居延三十井縣索關:吏所葆名縣73EJF3: 1.26、戍卒昭武步廣里不更楊當年廿九迎吏奉城官 五月辛丑南 ? 六月辛酉北嗇 73EJT37: 簡1.24左殘,原應為兩行,簡1.25亦為兩行。兩簡皆為肩水庫嗇夫兼行城尉事,簡1.25涉及吏民通關,簡1.24或亦如此,時間分別為建平二年(前5)、始建國二年(10)。此前,學者發現居延城倉長兼行都尉事,據此認為城倉與都尉府同處一地,[28]兼行城尉事的情況當與此類似,肩水庫嗇夫兼行城尉之事,兩者亦當同處A35遺址,便於處理相關業務。簡1.26為通關記錄簡,簡文顯示戍卒楊當前往城官迎取吏俸,可見城官當存儲一定的錢物,很可能設有專門的機構。另,前舉簡1.22顯示,肩水庫當在肩水塞南部。綜合諸簡及A35遺址的性質、地理位置,該地應屬肩水都尉轄區的總後勤基地,當設有“庫”。[29] 綜上考證,所謂的“都倉置”當位於A35遺址,該地設有都倉,亦設“庫”的機構。A35遺址駐有肩水都尉府和肩水城官,因其臨近弱水中下游兩大屯田區之一的騂馬屯田區,[30]故聚集儲存物資較為方便。而且,該地作為肩水都尉轄區的總後勤基地,負有供應及調配轄區內物資的任務,設立倉和庫亦屬事之當然。 二、居延地區的“置”北部甲渠、殄北、卅井三塞,負有拱衛居延屯田區的責任,其地位與作用與南部肩水都尉統轄諸候官塞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居延地區的地理環境較南部更為優越,適宜屯墾,故屯戍活動更為發達,人口更為繁盛。因此,居延地區的“置”設立更多,更為普遍,也更為分散。此前吳昌廉曾注意到吞遠置、第三置、遮虜置等的存在,惜未注意其設立背景及新沙置。下面結合倉及邊塞防禦組織體系,討論居延地區的“置”。 (一)吞遠置據下述諸簡,甲渠塞設有呑遠置: 2.1、?伐茭千石積吞遠置?EPT48:60A ?伐□茭千石積吞遠?EPT48:60B 2.2、?□吞遠置園中茭腐敗未以食?EPT52: 2.3、出粟大石廿五石車一兩始建國二年正月壬辰訾家昌里齊憙、就人同里陳豐,付吞遠置令史長EPT59: 2.4、?府……告居延甲渠鄣候:言主驛馬不侵候長業、城北候長宏□? EPF22:A ?居延,以吞遠置茭千束貸甲渠,草盛伐茭償,畢已,言。有EPF22:B ?將軍令所吞遠置茭言會六月廿五日又言償置茭會七月廿日建武六年二月?EPF22:C ?□□□驛馬伐茭所三千束,毋出七月晦EPF22:D 簡2.1兩面文字基本相同,據書式,似為某種楬,惜上下皆殘,無從明確判斷。簡2.2形制為單札,上下皆殘,據簡文,似為文書。這兩簡顯示,吞遠置存放不少的茭,且有園地。簡2.3形制為單札,始建國二年(10)正月有二十五大石的粟交給吞遠置令史長,令史長或在“屯遠置”當值。簡2.4為四面體的觚,殘損嚴重。據簡文,似乎吞遠置將一千束的茭貸給甲渠塞,可能未及時歸還,故上級機構發文追查。 與此同時,亦設立了吞遠倉,如下: 2.5、新始建國地皇上戊元年 ▓八月以來吞遠倉廪 吏卒刺EPT43:30A ▓吞遠倉吏卒刺EPT43:30B 該簡簡首為半圓形,且塗畫網狀格紋,當為楬。據簡文,吞遠倉給吏卒發放新莽地皇元年(20)八月以後的廩食,該楬當懸掛于這些原始記錄上,起到標識的作用。據下述諸簡,吞遠倉當設在吞遠隧。 2.6、吞遠隧倉新始建國?[31]戊三年亖月?EPT26:8 2.7、吞遠隧倉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EPT65: 2.8、■右吞遠部□?EPT10:19 2.9、·吞遠部建昭五年三月過書刾?EPT52:72 四枚簡皆為單札。前兩簡顯示,所謂吞遠倉,全名當為吞遠隧倉,即設於吞遠隧的倉。後兩簡,據其書式,當為某種簿籍的標題簡。吞遠部的得名,應該源於該部候長駐在吞遠隧。[32]吞遠隧作為吞遠部的候長治所,其規模當較一般亭隧為大,應有足夠空間設立倉、置。 (二)第三置著名的“候粟君所責寇恩事書”涉及了所謂的第三置,該簿書內容甚多,僅節引相關簡文如下: 2.10、直三千;大笥一合,直千;一石去盧一,直六百;索二枚,直千;皆在業車上。與業俱來還到北部,為業買肉十斤,直穀一石。到弟三置,為業?大麥二石。凡為穀三石,錢萬五千六百,皆在業所。恩與業俱來到居延後,恩 EPF22:25 該段簡文是寇恩自述為甲渠候粟君妻子業購買物資的花費,其中提到在第三置購買二石的大麥。比對吞遠置可知,第三置恐當設於第三隧。該隧材料甚多,僅引一枚如下: 2.11、第三隧長薛寄二月食三石二月辛亥自取EPF22:88 第三隧為第三部候長駐地,該部初元年間共統轄萬歲、卻適、臨之、第一、第二、第三等亭隧,習稱為萬歲部,第三部當為別名。[33]因此第三置亦設於第三部候長治所。不過,第三隧倉未見,倒有第三部傳舍的記載,如下: 2.12、?粟廿石 給萬歲傳舍 ./A8 柱馬食 若釋文無誤的話,萬歲部或設有傳舍。不過,傳舍之設,在弱水中下游流域的軍事防禦體系里似僅此一見。 此前,高榮據“第三置”的命名,推測當有第一置、第二置等。[34]目前尚未見到相關資料,而且弱水中下游流域的邊塞機構命名未必嚴格按照數字順序。對此說法,穩妥起見,不妨暫且存疑。 (三)新沙置據下述兩簡,卅井塞設有新沙置: 2.13、入粟給都吏壯卿檠戒塞上綏和元年六月庚戌新沙置卒馬受次東候長章 .15/A21 2.14、騎歸吞遠隧,其夜人定時,新沙置吏馮章行殄北警檄來,永求EPF22: 簡2.13形制為單札,出土于A21遺址,卅井塞懸索關即設在該地。[35]簡文顯示,次東部候長章將粟交給新沙置卒馬,具體數目未載。而次東部轄於卅井塞,[36]故新沙置轄於卅井塞的可能性較大。簡2.14為著名的“建武三年死駒案”卷宗的一枚,該簡顯示新沙置吏馮章承擔傳遞警檄的任務。弱水中下游的“置”,唯有此條明確顯示承擔了傳遞警檄的任務,似屬偶然現象。 (四)遮虜置材料還見有遮虜置與遮虜隧,如下: 2.15、禹令卒龐耐行书,夜昬五分付遮虜置吏辛戎?EPT65: 2.16、察微卒楊寅 遮虜卒張□ 制虜卒駟望卒□□ 逆胡卒蘇□ 望虜□沙頭卒范禹 驚虜卒王□.8/A8 前簡形制為單札,下殘。簡文顯示,一封郵書交付遮虜置吏辛戎手中,據“禹令卒龐耐行書”判斷,該簡並非習見的郵書刺或郵書課,或為普通文書,因此不足以據此認定遮虜置負責郵書的傳遞。後簡為寬木牘,分上下三欄書寫。共涉及察微、制虜、駟望、逆胡、望虜、驚虜、沙頭、遮虜等八所亭隧,其中前六所皆轄於甲渠塞,制虜、驚虜轄於吞遠部,察微、駟望轄於不侵部,望虜轄於臨木部,[37]逆胡不詳何部,[38]唯有沙頭轄於肩水塞。[39]據此,該簡所記亭隧並不一定皆轄於甲渠塞,遮虜隧亦無從考見其上級機構,遮虜置的問題亦無從解決。 綜上,北部居延都尉轄區,因其生產生活環境更為優越,屯戍活動較肩水地區更為發達,“置”的設置也比較多。所考見的“置”多設於部,而非候官,如甲渠塞設有吞遠置、第三置,分別位於吞遠部、第三部候長治所。據學者研究第三部(亦名萬歲部)位於河北道上塞南端,吞遠部位於河南道上塞北部,[40]皆在交通線上。此外,卅井塞設有新沙置。甲渠候官遺址出土資料最為豐富,而不見“置”的直接相關資料,恐怕甲渠候官並未設立這個機構。這點與南部的肩水、橐他、廣地候官不同。據學者研究,甲渠塞設置了上舉吞遠倉、萬歲倉外,亦設第廿三倉與候官倉。[41]材料顯示,吞遠置依託吞遠倉而建,卻不見第廿三置及候官置,頗為奇怪。 三、論“置”弱水中下游流域設立的“置”,因位於邊地,與亭塞相間,故其設立背景、職掌等,與懸泉置不同,鮮明地體現了該地區的特色。 (一)設立背景據前對都倉置、呑遠置等的討論不難看出,弱水中下游邊防系統內的“置”的設立往往依託于倉。“置”設在候官的原因之一,即是候官處有倉。據學者研究,甲渠候官設有倉,[42]肩水候官遺址亦發現吏卒廩食及穀物出入的簿籍,[43]固然不能絕對排除部隧上呈的可能性,但很大可能顯示該地亦當設倉。若此不誤,橐他、廣地及北部的卅井、殄北等候官,亦當設倉。 不過,候官儘管設倉,卻極少出現“候官倉”的字眼,這點值得注意。目前僅見下簡明言“候官倉”: 3.1、?受候官倉EPT4:57 該簡上殘,出土自甲渠候官遺址,倉當指甲渠候官倉。該地出土的其它涉及倉的簡牘,皆為入穀記錄。如下: 3.2、入粟大石二十五石 車一兩 始建國六年二月己丑將轉守尉?.32/A8 輸候官 3.3、入粟大石二十五石車一兩正月癸卯甲渠官掾譚受訾家茂陵東進里趙尹壯,就人肩水里郅宗EPT59: 前簡明確顯示運輸穀物到候官,後簡應當也是輸穀候官。雖然如此,兩枚簡皆未明確出現“候官倉”字樣。冨谷至認為,儘管部、候官等設有倉,但并無“倉”的建制,而材料中常見的倉長、倉丞、倉嗇夫等皆屬於肩水都倉和居延城倉的建制。[44]這一點堪稱卓見,倉確為候官的附屬設施,並非獨立的機構。倉平時的管理工作,由令史、尉史等負責,除前舉2.3令史在呑遠置當值外,其它簡例甚多,暫舉兩枚如下: 3.4、建始二年十月乙卯朔丙子,令史弘敢言之:迺乙亥直符,倉庫戶封皆完,毋盜賊發者,敢言之。EPT52: 3.5、?五月戊寅尉史蒲敢言之,迺丁酉直符,倉庫戶皆完,毋盜賊發者?之 .9/A8 令史、尉史通過直符的形式,巡視倉庫府藏等設施。未在A8遺址見到倉嗇夫、倉佐的身影,原因或即在此。 (二)職掌此前學界對秦漢時期“置”職責的考察,往往焦點集中于懸泉置,認為“置”兼具文書傳遞與吏員招待的功能。[45]實際上,這種看法可能不盡準確,弱水中下游流域的“置”,其功能與任務主要集中于物資供應。目前所見,與“置”相關的簡牘,絕大多數涉及的都是物資出入,如前舉1.10、1.11、1.13、2.3等簡涉及糧食。下述四簡涉及雞、狗及佐料: 3.6、入狗一枚元康四年二月己未朔己巳,佐建受右前部,禁姦卒充輸,子元受,致書在子元所5.12/A33 3.7、入小畜雞子五枚元康四年二月己未朔己巳,佐建受左後部,如意隧長奉親卒外人輸,子元受10.12/A33 3.8、?六月乙丑佐博買鷄五枚破虜?.5/A33 3.9、二月壬子置佐遷市薑二斤.8/A33 四簡形制皆為單札。前兩簡顯示,元康四年(前62)二月己巳這一天,佐建分別接收右前部的狗和左後部的雞蛋。簡3.6顯示,物資出入時當製作“致書”,作為憑證,簡3.7可能省略未載。雖然時間相同,事主皆為佐建,細察兩簡筆跡,簡3.6細瘦劣弱,簡3.7嚴謹工整,而且,枚、佐、建、部、元、受等字的架構筆畫迥然有別,顯非同一人書寫,當為不同人記錄而留下的案底。簡3.8上下皆殘,書式與前兩簡相似,亦涉物資出入。該簡佐博,與前舉1.9、1.10當為同一人。3.7、3.8兩簡雖未明言為置佐,結合“置佐博”省作“佐博”的現象,以及兩簡物資出入的種類及文書性質判斷,當為置佐。3.9上下完好,上端似有刮削痕跡,置佐遷購買兩斤的薑。據上節所言肩水候官設有“置”的情況,四枚簡當由駐在A33遺址的置所留下的文書,而非由設於其它地方的“置”呈給肩水候官的文書。 此外,前舉2.1、2.2、2.4等涉及茭的出入,下述兩簡亦如此: 3.10、入錢六三月丁巳佐博賣茭二束河東卒史武賀所.2/A33 3.11、入錢六……月乙酉佐博賣茭二束魏郡侯國令史馬穀所,直.6/A33 兩簡皆為單札,儘管均涉佐博,但墨色濃淡迥異,筆跡似亦不同。末簡“入錢六”下面似有一段文字,當是刮削不淨而遺留的。兩簡書式相同,紀月日而不紀年,與前舉簡3.6、3.7不同。3.6、3.7兩簡可能為臨時性物資出入,故詳載年月日,而此兩簡或為日常性物資出入,且數額不大,故僅記月日。兩簡佐博,或即前舉諸簡所涉置佐博。此外,“置”亦須向肩水候官報告錢物出入,如下簡: 3.12、甲戌置左博敢言之:謹移稍入□? ?肩水候.10A/A33 該簡左殘,似為兩行。上端大書“肩水候”,下面接續置佐博的呈文。“稍入”下所缺之字似為“錢”,稍入錢是邊塞的一種非固定收入。[46]簡首大字書寫“肩水候”似指其呈送目的機構,若此不誤,則該簡及相關簡牘亦是呈送給肩水候的文書。此外,下述諸簡,亦涉及“置”: 3.13、?一千付置佐?.7+.48/A33 3.14、?置佐博受就人井客?.5/A33 3.15、?佐博受所賣酒二石.9/A33 3.16、?八月辛巳置佐遷買□二□?.10/A33 3.17、?月己巳置佐禹市?73EJT28: 3.18、?日置佐威受卒趙詡73EJT37:1 六簡皆為單札,均涉及錢物出入。3.15未明言置佐,比對前舉諸簡,亦應為置佐。 綜上,絕大多數相關資料,均與物資出入有關。如前所述,該地區的“置”往往依託倉而設立,這一點亦吻合其主要職掌。而與文書傳遞有關者,僅上舉2.14置吏行警檄、2.15置吏行書,以及下簡: 3.19、□張掖大守章詣居延三月丁酉起 □□□史龐土印詣居延三月癸巳起三月乙巳夜過半時受都倉置卒不椑已 ……□周漢印詣居延三月己亥起 86EDT65:2 該簡為寬木牘,據簡文及書式判斷,當為某種文書傳遞記錄。加在一起,目前僅見三簡涉及文書傳遞。但嚴格上講,2.14傳遞警檄屬於突發事件,與一般的文書傳遞不同,而2.15書式亦與常見文書傳遞有別,因此,真正涉及文書傳遞的恐怕只有3.19一枚。因此,很難說“置”在物資供應之餘,還要負責傳遞文書。 此外,下簡是對“置吏”職掌的最好說明: 3.20、置吏宋吏壽掌廚傳過客驛馬73EJF3: 該簡出土自A32遺址東側關門房屋內的隔間,性質難以判定。據簡文,置吏負責“廚傳過客驛馬”,可分為廚、傳、過客、驛馬等四個義項,結合前據諸簡,前三者無疑表明置吏涉及物資供應,包括供應飲食、提供住宿等。“掌驛馬”則有兩種可能:(1)飼養驛馬;(2)為過往驛馬提供飼料。無論哪一類,置吏似均不直接承擔文書傳遞的任務。此前,陳偉曾據秦及漢初相關律令,認為傳置與行書無關,[47]弱水中下游流域的“置”似亦如此。這點與漢代敦煌郡效榖縣的懸泉置大不一樣。懸泉置漢簡尚未正式出版,目前為止僅零星刊布部分釋文,據學者初步勾勒,懸泉置不僅負責過往使者、官員及其隨從在飲食、交通、住宿的服務,亦負責東西向政令、文書的傳遞。[48]之所以有此差別,很可能因弱水中下游流域亭隧建置齊備,文書傳遞由專門的亭隧負責,[49]無需“置”人員兼差,而懸泉置處在郡縣民政體系內,並無亭隧建制,故承擔任務亦多樣化。 如果回過頭來再看肩水、居延地區“置”的分佈特點,即很容易理解。肩水地區的三個候官,都位於弱水沿岸的交通線上,這一帶的綠洲較少,沿河呈條形分佈,而烽燧通常位於戈壁與綠洲的交界處,距交通線尚有距離,因此負責物資供應的“置”理應也設在交通線上。北部居延地區,則分佈有大片綠洲,甲渠候官塞的兩條烽燧線——河南道上塞與河北塞——位於交通線上,故“置”緊靠烽燧線設立,而不一定設在甲渠候官,在情理上是講得通的。 (三)置佐如前所述,“置”依託于倉而設立,但相對於倉的附屬地位,“置”是個獨立的機構,有自己的職官建制,如前舉諸簡中頻頻出現的置佐,以及偶爾一見的置輿。吳昌廉、高榮皆認為,“置”設有嗇夫、佐等。[50]一般意義上可能如此,但弱水中下游流域的“置”,僅有一例出現嗇夫。如下: 3.21、河平二年九月壬辰朔 肩水置嗇夫光詣官? 86EDT8:2+26 該簡明確出現置嗇夫一職,從簡牘出土自肩水候官遺址判斷,此處“肩水”或指肩水候官,“肩水置嗇夫”或許就是設在肩水候官的置嗇夫。[51]此外,下簡疑似出現了置嗇夫: 3.22、?朔壬子,肩水守候橐他塞尉舉敢言之:謹移穀?言之.5A 嗇夫去疾.5B/A33 該簡上殘,紀年不存。據簡文,橐他塞尉守肩水候,上呈某種穀相關的簿籍,當涉穀物出入。簡背具名為“嗇夫去疾”,顯示該文書當由其草擬負責。如前所述,候官處所設的倉僅為附屬機構,並未設置倉嗇夫,而且目前肩水候官亦未見其它機構的嗇夫,結合肩水候官設有“置”這個機構的事實,推測該簡嗇夫或為置嗇夫。另,前舉1.10、1.11、1.13、2.3等簡,“置”皆涉及穀物出入,該簡亦如此,故“去疾”為置嗇夫的可能性比較高。 總而言之,置嗇夫出現的頻率極少,而置佐卻頻頻出現。一般情況下官嗇夫級別較官佐更高,理應出現更多,何以如此呢?睡虎地秦簡顯示,秦代即存在“小官無嗇夫”的現象,[52]尹灣漢簡顯示,成帝元延年間東海郡領有的38個縣邑侯國中就有17個設官佐而無嗇夫。[53]據學者研究,隨著直屬于長吏的史類吏員地位與作用的逐漸擴大,到西漢中後期,嗇夫類吏員已多為前者所取代,[54]弱水中下游流域置佐頻現而嗇夫不見的現象與這一觀點若合符節,很可能簡3.22的時代較早,尚設有置嗇夫,後期則僅設置佐而無嗇夫了。 此外,前舉簡1.2、簡1.8等候文書的落款均為置佐,表示文書由置佐負責。一般而言,候的文書落款多為令史、尉史,或兩者皆有,或兩者有一,間以出現掾和士吏,[55]出現“置佐”的情況較為少見。不過,如前所述,因“置”設於候官,故距離相近,偶爾負責候的文書亦可理解。除上舉簡1.2、簡1.8由“置佐”負責外,縣署中的倉佐亦偶涉文書事,如下: 3.23、河平四年二月甲申朔丙午,倉嗇夫望敢言之:故魏郡原城陽宜里王禁自言:二年戍,屬居延,犯法論,會正月甲子赦令,免為庶人,願歸故縣。謹案:律曰:徒事已毋糧,謹故官為封偃檢,縣次續食,給法所當得。謁移過所津關,毋苛留止。原城收事。敢言之。 二月丙午居令博移過所如律令掾宣嗇夫望佐忠73EJT3:55 3.24、?□四年十二月丁酉朔己亥,觻得令建守丞安昌敢言之:謹移十月□?之57.10A 掾宗守嗇夫延年佐就57.10B/A8 前簡為私傳。魏郡原城縣王禁在居延服役期間犯法,可能分派入居延縣倉勞作,後逢赦令而免為庶人,打算回到原籍,故倉嗇夫向縣廷申請。該文書具名“掾宣嗇夫望佐忠”,掾當為縣令的屬吏,嗇夫望與文書申請者倉嗇夫望同名,當為同一人,佐忠當即倉佐。之所以如此署名,當因該文書涉及倉,故由倉申請,呈給縣廷批准。後簡年號殘去,查曆日當為元始四年(公元4年)。觻得令建、守丞安昌上呈十月份的某種簿籍,具名“掾宗守嗇夫延年佐就”的格式與前簡相同,嗇夫、佐聯袂出現,亦當為同一個機構的官吏,為倉的可能性比較大。需要指出的是,上舉諸佐並不是常見的書佐。據學者研究,東漢中後期,書佐存在於縣廷,或許與之同級的候官亦有書佐,但西漢並無材料顯示縣或候官存在書佐。[56]因此,西漢時候官和縣中存在的佐,可能專掌“官”,與後期掌文書事的書佐大不相同,但因為駐地相近事務相關,亦偶涉文書事,長此下去,發生由“佐”而“書佐”的制度演變。或許,可從這個角度理解東漢以後書佐的產生。 附帶指出,著名的“甘露二年御史書”雖經眾多學者的考釋梳理,但第二枚簡中太守府轉發語的落款“掾佷守卒史禹置佐財”,似未得到正確的理解。文書太長,節引相關部分如下: 3.25、嚴教屬縣官令以下,嗇夫、吏、正、父老雜驗問鄉里吏民賞取婢及免婢以為妻,年五十以刑狀類麗戎者,問父母昆弟本誰生子,務得請實、發生從迹,毋督聚煩擾民。大逆同產當坐,重事,推迹未窮,毋令居部界中不覺。得者書言白報,以郵亭行,詣長安傳舍。重事,當奏聞,必謹密之,毋留,如律令。 六月張掖大守毋適、丞勳敢告部都尉卒人謂縣:寫移書到,趣報,如御史書律令,敢告卒人。/掾佷守卒史禹置佐財73EJT1:2 關於落款“掾佷守卒史禹置佐財”,通行的斷句是“掾佷、守卒史禹、置佐財”,並將置佐理解為某種佐史。[57]後來學者據前引簡1.4、1.9及懸泉漢簡,認為置佐很可能是驛站傳置的佐。[58]如果拋開該文書單論置佐,將其理解為驛站傳置的佐,自然可以成立,不過,具名“掾佷守卒史禹置佐財”的文書是由太守府發出的,而傳置一般設於縣級機構,不見於太守府及同級機構,[59]因此理解為置佐似乎不妥。結合漢簡中頗出現人名為“可置”的情形,[60]落款“掾佷守卒史禹置佐財”應斷句為“掾佷、守卒史禹置、佐財”,即守卒史名為“禹置”,佐名為財。太守府發出的文書不乏署名“佐某”和“書佐某”的用例,[61]與此相吻合。 四、餘論綜上,漢代弱水中下游流域的邊防系統,亦即張掖郡肩水、居延都尉轄區,普遍設有“置”這個機構。南部肩水地區,“置”設於各候官。北部居延地區則設於候官塞統轄的某些候長治所。一般而言,“置”均依託于倉而建立。肩水都尉府和肩水城官所在地——A35遺址,設有總後勤基地性質的都倉和庫。所謂都倉置,當亦設在該地,直屬於肩水城官。 該地區的“置”,主要負責廚傳及過往吏民驛馬等物資供應及相關需求,極少傳遞文書,因該地區亭塞相間逶迤不絕,文書傳遞由亭隧卒負責,不勞“置”人員兼差。總體而言,在弱水中下游流域邊防系統中,“置”屬於隱在幕後的後勤部門,出現的頻率並不高。該地區“置”的負責者,一般為置佐,嗇夫極少出現。材料所見,置佐因與塞候共處一地,或因業務相關,偶爾亦負責候文書的起草。當然,弱水中下游流域的民政機構,如肩水縣、居延縣等,是否設有“置”,其特點如何等問題,因資料缺乏,尚無從研究。 附帶指出,日本學者永田英正所示範的文書簡典型研究方法——集成法,據本文對“置”的研究,亦須做出必要的調整。永田氏方法的基本思路就是集成同一出土地的文書,按照書式不同分類定名,在此基礎上討論簿籍的製作、流傳、處理等過程,藉此揭示了候官的職能與作用。其默認的前提是,一個遺址僅駐一個機構,故該遺址出土簡牘皆為某機構遺物。綜觀永田所集成的文書的出土地——A8、A33、P9、A10、A35,前三者皆為候官遺址,但據本文研究,所謂候官並非只有一個機構,至少就肩水候官而言,還設有“置”這一小型機構。前舉數枚A33遺址出土“置”的簡牘,永田英正不作區別集入肩水候官文書。[62]當然,就肩水、橐他、廣地候官而言,“置”設在候官,其簡牘屬於廣義上的候官文書,永田氏的處理似乎也無可厚非。但相較而言,甲渠候官即未設“置”,因此甲渠候官與肩水候官遺址的文書在種類上就存在不同,籠統討論候官在文書處理上的職能與作用,未見其宜。筆者以為,若要深入研究候官的職掌與功能,需要進入候官內部,對候官遺址的簡牘文書做出更精細的區屬。[63]總而言之,通過集成方法研究候官或其它機構的職掌與作用,首先需要明確哪些材料屬於該機構的遺留物,必須界定清晰才可進行下一步。 TheZhiofthedefensesystemaroundtheRuoRiver’smiddle-lowerreachesduringtheHanDynasty ABSTRACT:TheJianshui(肩水)andJuyan(居延)CommanderyofZhangyeprefectureinHandynastywaslocatedinlowerstreamofRuoriver(弱水),whichbelongedtothemilitarysystemanddefendedagainsttheHuns.TheareasetuptheZhi(置),whichrelyedonwarehouseandsuppliedmaterials.TheJianshui(肩水)、Tuota(橐他)、Guangdi(廣地)Houguan(候官),andtheJianshuichengguan(肩水城官)andsoonsetuptheZhi(置).TheZhi(置)intheJuyan(居延)Commandery,werelocatedattheBu(部)orSui(隧).TheZhi(置)intheRuoriver(弱水)lowerstreamdidn’ttransmitofficialpapers,whichwasdifferentfromtheXuanquanzhi(懸泉置).ThepaperdiscussesthefamousGanluernianyushishu(甘露二年禦史書),andmakesareflectiononthemethodaboutHouguan(候官)documentswhichwasinitiatedbyYongtianyingzheng(永田英正). KEYWORDS:ZhilowerstreamoftheRuoriverHouguanZhizuo [1]《史記》卷九四《田儋列傳》(北京:中華書局,年),頁。 [2]《史記》卷一〇《孝文本紀》,頁。 [3]張傳璽:懸泉置、效榖縣、魚澤鄣的設與廢,收入《張維華紀念文集》(濟南:齊魯書社,年),頁-;何雙全:漢代西北驛道與傳置——甲渠候官、懸泉漢簡〈傳置道里簿〉考述,《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年第1期,頁62-69;宮宅潔:懸泉置及其周邊——敦煌至安西間的歷史地理,原刊《シルクロ-ド学研究》22號,年,此據中譯,刊於《簡帛研究》,年,頁-;張經久、張俊民: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出土的“騎置”簡,《敦煌學輯刊》年第2期,頁59-73;張德芳:懸泉漢簡中的“懸泉置”,《簡帛研究》,年,頁-;李岩云:年敦煌小方盤城出土的一批簡牘涉及的相關問題,《敦煌研究》年第2期,頁-;趙岩:論漢代邊地傳食的供給——以敦煌懸泉置漢簡為考察中心,《敦煌學輯刊》年第2期,頁-;李并成:漢敦煌郡境內置、騎置、驛等位置考,《敦煌研究》年第3期,頁70-77;呂志峰:敦煌懸泉置考論——以敦煌懸泉漢簡為中心,《敦煌研究》年第4期,頁66-72;李并成:漢酒泉郡十一置考,《敦煌研究》年第1期,頁-;張俊民:西漢敦煌郡縣置名稱考、懸泉漢簡所見“置嗇夫”人名綜述,收入作者:《敦煌懸泉置出土文書研究》,頁-、-。 [4]發源於祁連山,流經青海、甘肅、內蒙古,最後注入今額濟納旗蘇股淖爾和嘎順淖爾尾閭的這條內陸河,在甘肅境內,今天一般稱為黑河,內蒙境內稱為額濟納河。為表述方便,依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本文統稱為弱水。 [5]吳昌廉:漢“置”初探,《簡牘學報》第十五期(年),頁1-22;高榮:論秦漢的置上、下,分別刊於《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5、6期(年),頁60-65、59-65。 [6]本文所引居延舊簡,.20號簡之前均引自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壹、貳、叁)(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年),其它居延舊簡引自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年)。圖版參考新刊紅外線圖版、勞榦《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年)及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補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年),部分圖版亦核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漢代簡牘資料庫(
|
当前位置: 金塔县 >漢代弱水中下游流域邊防系統中的ldqu
时间:2021/3/23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贵阳一中金塔英才学校面向社会招聘各学科优
- 下一篇文章: 中国中铁全公司精彩资讯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