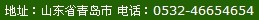|
▲图片来自网络 [摘要]历史上暹罗从吴哥王朝借鉴了神化国王的思想和政治统治,但王权发展却别具一格,体现为法王文化。吴哥神王文化研究新作《“翻搅乳海”:吴哥寺中的神与王》指出,吴哥寺搅乳海浮雕中有传统样式从未出现的角色——海底蛇王和中轴线上最高处手执器具的飞翔天神,分别是作为时间化身的蛇王舍沙和手执与创世关联的因陀罗网的天神因陀罗,二者发挥扶持神王的功能。然而当视野在时空上拓展,中南半岛以王权崇拜为核心的礼法文化提供了另一种解答:海底蛇王是基于本土女权文化礼俗——以那珈图腾为符号——的表达;手执器具的天神则是法的使者正在须弥山顶放置法典,是尚法的创意。搅乳海浮雕设计创意揭示了泰国法王思想的源头实际上存在于鼎盛时期的吴哥王朝。 [作者简介]吴圣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关键词]泰国;法王思想;吴哥寺;神王;搅乳海浮雕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年第2期。 一问题的提出 泰国的王权崇拜举世闻名,每一部宪法均规定国王神圣不可侵犯,世人视“国王是神—佛—国王三者的完美统一”[1]。自泰民族第一个政治国家素可泰(—)建立直到曼谷王朝(至今),在多年的历史中,王权崇拜逐步形成具有泰民族特性的文化传统。据史料记载,阿瑜陀耶时期(—),统治者借鉴古高棉的政治统治制度,引入神化国王的思想[2],但王权的发展却走上一条与古高棉神王(Devaraja)不同的道路。泰国国王虽位高权重,但有十王道、四德行、十二职责等法(Tham)的约束[3],以做法王(Thamraja)为旨归。年民主革命后,国王成为名誉国家元首,没有实权,但仍深孚众望,被视为正法的代表,左右政治的发展。已故国王普密蓬在位时(—)尤为显著地体现了这种王权特征。 泰国国王的神性并非神王的神通性,而是作为法王的神圣性。学者们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一般 首先,该书运用的资料丰富多样,特别是专业资料方面涵盖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古印度文献资料以及古代文史资料。例如,关于浮雕创作的故事版本依据,该书比较了多部古印度文献资料。搅乳海故事源自印度教文化,在古印度多部圣典中都有描述,包括史诗类《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也包括往世书类如《薄伽梵往世书》《毗湿奴往世书》《火神往世书》和《鱼往世书》等,不同版本的故事或多或少有所差别。在对浮雕图像信息进行比较筛查之后,该书认为,浮雕的场景大部分取材自《薄伽梵往世书》,同时也从各个版本故事及其它文献中摘选符合实际表达需求的段落、场景和人物。关于浮雕的形制,该书对同主题作品进行广泛的实物比较,总结出其与传统样式的区别,指出吴哥寺设计者创新性地添加了一些搅乳海故事中没有的角色,并对其含义和功能加以诠释。 其次,该书分析浮雕反映的秩序内涵,提出了具有突破性的观点。该书把作为宇宙空间和时间秩序媒介的太阳运用到吴哥寺面朝西、逆时针回廊这两个重要建筑特点的讨论中。该书把自然界太阳直射点南北移动形成一年的季节点、吴哥寺立面塔楼布局与浮雕神魔队伍角色相对应,对吴哥寺建造者宣扬“君权神授”的艺术表达进行了精彩的论述,合理地解释了寺庙朝西的非陵寝的设计意图;并把太阳直射点的南北移动与寺庙立面和浮雕体现的印度宇宙观“南混沌、北秩序”的时空秩序相结合,解释人逆时针从代表混沌失序的寺庙立面南翼行进,依次经过浮雕中轴南面阿修罗队伍、中轴保护神毗湿奴造型,进入代表秩序的天神队伍和寺庙立面北翼,在行进的过程中感受国王作为秩序的捍卫者、混沌失序的惩罚者和新时代引路人的神圣。此外,该书对比吴哥寺主人苏利耶跋摩二世(公元—/年在位)与杰出的先王苏利耶跋摩一世的身世,指出两者并无亲缘关系,但前者却追随后者以苏利耶为名号,即自比太阳,作为秩序的代表,其用意与浮雕主体呈现的强烈的秩序感相互印证,进而推翻前人关于吴哥寺为单纯的寺庙或陵墓的臆断,进一步丰富赛代斯、费利奥萨(JeanFilliozat)从功能角度提出的“墓庙合一”的观点,认为吴哥寺是纪念吴哥国王的神王精魂的墓庙合一纪念碑。 第三,该书对浮雕中轴线上各造型给予特别的 上述关于吴哥神王文化的研究包括最新成果《翻》,都基本围绕着吴哥当时当地进行研究。笔者认为,要对吴哥神王文化作更全面的考察,对吴哥王朝势力范围内的泰国、老挝等地所受影响的研究也不可忽视。当视野在时空上拓展,我们看到,中南半岛维护社会秩序的特点——以王权崇拜为核心的礼法文化,为浮雕中的海底蛇王及飞翔天神的含义提供了另一种解答。本文笔者将对此进行论证,从而揭示泰国法王文化与吴哥神王文化的渊源,同时希望对吴哥神王文化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二海底蛇王的隐喻:古高棉王权崇拜的礼俗基础 如图1所示,在浮雕的最底部,即乳海底部横卧着一条头戴王冠的七头巨蛇,《翻》推翻前人关于其为婆苏吉(Vasuki)——缠在曼陀罗山腰参与搅乳海的蛇王的猜测,认为根据《摩诃婆罗多》版故事的说法,它是婆苏吉之兄,即拔取曼陀罗山作为搅棒的阿难答·舍沙(AnantaSesa),它曾遵照梵天的嘱托,以身躯承托和固定整个大地。 《翻》从梵语词根sis意指“剩余”、“留存”探索舍沙命名的内涵,即不受时间约束、超越宇宙的一切存在,是时间神力的化身。作者引用美国学者曼尼加的测算加以论证,即从吴哥寺主通道的西面起点跨越护城河为肘“[10],从跨过桥面后的点转向南北两端都是肘,从南北两端转向东方至寺庙的南北中轴相交点都是肘,从南北两个相交点分别向寺庙中心台基移动至到达台基这两段相加是肘,这些距离长度数字分别对应宇宙周期中的第四个阶段“伽利期”的,年、第三个阶段“二分期”的,年、第二个阶段“三分期”的,年和第一个阶段“生成期”的1,,年(如图2所示)。《翻》基于对应的时期排序与人从寺庙外进入中央圣殿的行进次序相反以及中央圣殿的宇宙生成期含蕴,指出这一路径以长度数字象征一个完整的宇宙周期,正是时间主宰舍沙在吴哥寺中的表现形式,解释作为时间化身的舍沙亦参与到扶持神王的活动中,是从最大的宇宙周期层面上表达神王开启新时代。 不可否认上述曼尼加的测算数字与宇宙周期四个时段年数的精确对应绝非巧合,《翻》的分析揭示了寺庙设计的精妙,但是设计者把用意隐含在数字对应关系中,考古也未曾发现相应的文字说明,在资讯不发达和社会文化知识水平低下的年代,进入到中央圣殿的人能否参透设计的精妙,感悟舍沙作为时间化身的隐喻,进而萌生特别的神圣感呢?没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印度宗教哲学基础的人恐难以做到。因此笔者认为,即便设计者别具匠心,海底蛇王的设计也必须基于时人对蛇王的普遍认知,只有当观者看懂浮雕,产生思想的共鸣,艺术创作才能实现最高的价值。 那么,古高棉人对蛇王的认知是怎样的呢?笔者曾对中南半岛的蛇王信仰做过专门的研究。从起源来看,至少在公元前年之前的印度河城市文明时期,在古印度与中南半岛原始母系社会的接触中,古印度蟒蛇崇拜对中南半岛产生影响,蟒蛇一词“那珈”(Naga)被借入中南半岛。从其文化内涵来看,那珈是蕴含女性崇拜的图腾[11]。东南亚许多传说中,那珈是女性,比如泰国传说中,素可泰王族的先祖帕銮的母亲是那珈女;洪沙瓦底(缅甸的古都)建国故事中,那珈女变为少女和国王结婚生子;柬埔寨的那珈女参与建国的传说则更为著名,扶南(柬埔寨古国,公元前1世纪—公元6世纪)建国传说叙述道,婆罗门憍陈如娶了那珈王(蛇精)之女即扶南女王,从而统治了扶南[12]。笔者曾撰文分析扶南建国故事的文化内涵,揭示其反映出在古代中南半岛女性备受重视[13]。中南半岛传说中的那珈有三个特点:(1)具有土著人的象征;(2)是土地之主,掌管水源;(3)是一种信仰[14]。可见,蛇王那珈信仰是中南半岛广为人知的图腾崇拜,那珈是民众心目中生命的主宰,是原始母系社会女性崇拜的符号。 古印度对东南亚文明的影响是持续的。后印度河城市文明时期,印度教和佛教在古印度的兴起和发展中均吸收了当地的民间信仰,其中包括那珈。那珈融入到史诗故事或佛教故事中,随着印度教和佛教在东南亚的传播而再次传入东南亚,但已沦为工具和配角,用以凸显主神或佛主的至上地位。不过,中南半岛民众对那珈主宰生命的原初认知仍然根深蒂固。元代曾出访真腊的周达观在其游记《真腊风土记》中记载一则金塔传闻:“其内中金塔,国主夜则卧其上。土人皆谓塔之中有九头蛇精,乃一国之土地主也,系女身。每夜(则)见国主,则先与之同寝交媾,虽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与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见,则番王死期至矣;若番王一夜不往,则必获灾祸。”[15]当时印度教在东南亚传播已有千年以上,但仍有这种印度教寺庙的金塔被蛇精而非天神把持的传闻,表明民众对传统那珈信仰的认知度之深,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那珈形象主宰着真腊装饰艺术[16]。那珈造型在古高棉宗教艺术中有单独刻画的,如寺庙栏杆扶手、圣水池边框、山墙飞檐等;也有融合在印度教或佛教故事造型艺术中的,如搅乳海雕塑、那珈护首佛像等。由于民众对那珈原初的文化内涵记忆深刻,自然会把单独出现的那珈造型当成本土的图腾,甚至会影响其对融入到史诗或佛教故事中的那珈的判断,比如吴哥城门搅乳海石像中的搅绳龙王那珈,民间传说是柬埔寨始祖和女保护神的形象[17]。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浮雕底部的蛇王与充当搅绳的蛇王婆苏吉是古印度文明两个传播阶段的产物,后者是印度教(或称“婆罗门教”)兴起后传入东南亚的故事中的配角,而前者则属于早在印度河城市文明时期就已经传入东南亚的那珈信仰。东南亚本土文化与文明发展的模式是各国本土文化大量保存并发展,同时根据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对外来文化有选择地吸收和改造[18],被吸收和改造的外来文化经过千百年的融合积淀,又固化为本土传统,那珈信仰就是这种模式的体现。统治者为巩固王权,既保存本土文化,又借鉴印度教神王文化,创作了搅乳海浮雕。浮雕底部的蛇王体现中南半岛本土文化,设计基于古老的隐含女性王权崇拜的共识,是对传统礼俗的尊重。至于进入圣殿路线距离数字、宇宙周期年数与舍沙隐喻关联的精心设计,民众不一定能轻易理解。但当人们站在浮雕前,心中升起的对传统观念中掌管水源、主宰万物的那珈的虔敬,与舍沙作为时间的化身、超越宇宙一切存在的最高主宰而应该获得的敬仰是相通的。 三手执器具的飞翔天神:古高棉法王理念的推崇 如图3所示,浮雕中轴线的最顶端是一个飞翔的天神,正将手中的“器具”[19]摆放在须弥山顶。《翻》的作者认为,这是因陀罗神(Indra)在须弥山顶放置因陀罗网。此推断合乎逻辑,但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 首先,把飞翔天神认定为因陀罗的理据不充分。识别印度教天神通常通过故事场景、特殊长相、身姿、坐骑或者手持的器具等。“这位天神身量较小,浑身上下的装饰也未见特殊”,天神手中握的不是因陀罗标志性的金刚杵,而是一件以往作品中未曾出现过的器具,身姿也非因陀罗传统的屈膝盘坐[20],但《翻》断定其是因陀罗的原因有二:一是《摩诃婆罗多》中提及;二是赛代斯的认定。笔者以为,这两条理由都不充分。第一,该场景只在《摩诃婆罗多》中简要提及:当“搅棒”曼陀罗山被放上巨龟背甲之后,因陀罗又将一件“器具”(yantra)放到了山顶之上[21]。仅以一个并非浮雕设计主要依据的故事中的情节为理由,并缺少进一步的取材合理性论证,证据过于单薄。第二,赛代斯认定的根据是因陀罗居所在须弥山顶,“鉴于高棉传统中须弥山与曼陀罗山是混为一谈的,因此出现在山顶处的天神无疑是因陀罗”[22]。赛代斯的推论过于武断,有能力在空中飞翔甚至超越须弥山顶的天神不止因陀罗一尊,而且此判断导致解释因陀罗在故事与浮雕中的地位时出现矛盾。在搅乳海故事中,毗湿奴主宰战局。天神获胜归功于毗湿奴,就连《摩诃婆罗多》描绘的神魔大战给人印象最深的也不是天神,而是毗湿奴[23]。《翻》指出,吴哥寺浮雕所刻画的神魔主要取材自往世书故事,天神之首因陀罗用金刚杵奋勇杀死无数强悍的阿修罗首领,为天神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显示了因陀罗的重要性,因陀罗与毗湿奴相互配合成就伟业,因此两尊大神在浮雕中应有相匹配的重要位置。毗湿奴位于中轴线的中部,位置显赫。因陀罗本应手擎蛇尾站在天神队伍末尾,《翻》认为该位置太不显眼,与其在文本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相匹配,而中轴线是图像最重要的视觉区域,排除中轴线其他已知的角色,位于最上方的飞翔天神当是因陀罗[24]。《翻》还认为,这位身处中轴顶端的天神,身份极有可能高于其他浮雕角色[25]。然而,即使不考虑毗湿奴在史诗类故事中的主宰地位,按照往世书类故事描述,毗湿奴与因陀罗功劳相当,浮雕中后者的位置高于前者则是矛盾的。为化解此矛盾,顺着《翻》分析的逻辑,我们看到“因陀罗就是十全十美的神王偶像,在天空他是太阳,在搅乳海故事中他是因陀罗,在吴哥王朝则是苏利耶跋摩二世”[26],当之无愧处于中轴最高处。但这个解释却又引出另一个矛盾,即与吴哥寺原名“毗湿奴世界”(VrahVisnulouk)[27]不相符。 第二,将飞翔天神手中器具推断为因陀罗网,缺乏根据和完整的解释。《翻》的作者认为,因陀罗网分为两部分,上部分呈矩形位于山顶,下部分罩在山体上。依大乘佛教经典记述,须弥山是世间秩序的集大成者,具有创造力的因陀罗网覆盖其上,等于覆盖整个宇宙。因陀罗网对物质世界的创造也须以宇宙极点[28]作为起始和中心,器具放置之后,搅乳海的创世活动才开始。《翻》从经典记述推导出因陀罗用网罩住须弥山,虽然行为意义相通,但缺乏证据显示民众对此有认知基础。手持因陀罗网而非金刚杵的因陀罗造型在整个吴哥造型艺术中极为少见,苏利耶跋摩二世之后,也没有证据显示因陀罗网广为人知。阇耶跋摩七世(—年在位)建造的巴戎寺的搅乳海浮雕虽然继承了吴哥寺飞翔天神场景,但天神手中也并没有类似形状的因陀罗网[29]。《翻》的作者也对其在神王文化传承中的失落表示好奇。更重要的是,作者未对因陀罗网的形制做出解释,包括器具内部十分浅淡的横线纹路、罩在山体上半部的纱网式和下半部的垂线式。然而器具形体为长条矩形,无论作为山体网状罩纱原初叠放时本该有的柔软形状,还是作为罩纱披下后的收口,都难以通过想象关联,这种直观的印象会直接导致观者对其为因陀罗网的质疑。 笔者认为,既然飞翔天神场景是设计者的创意,不妨在吴哥寺回廊浮雕的整体构思中探索其创作意图。回廊浮雕的主要内容包括《摩诃婆罗多》的俱卢之野决战、《罗摩衍那》的兰卡之战、苏利耶跋摩二世行军图、阎魔的审判、搅乳海、毗湿奴大战阿修罗、克利希纳(Krishna,毗湿奴的化身之一)大战魔王班纳(Bana)和神魔大战等,其核心理念可以提炼为弘扬正法,正义战胜非正义。天神是善的,阿修罗和魔怪是恶的,搅乳海与神魔大战无需多言,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里面都是保护神毗湿奴的化身作为正义的一方最终获胜;阎魔的审判理所当然以正法为依据;苏利耶跋摩二世的军队为正义而战,这一点《翻》的作者也结合史实对弑亲篡位、崇尚武力的苏利耶跋摩二世标榜自身正义的可能性进行了合理的论证[30]。所以,如果说飞翔天神场景隐含弘扬正法的思想,不仅切合浮雕的主题,而且弘扬正法的哲理,对于民众来说也更通俗易懂。 吴哥寺设计者、博学之士婆罗门提婆伽罗班智达(Divakarapandita)把弘扬正法的思想融入飞翔天神的设计中合情合理。首先,古代中南半岛人关于法的来源认知中有飞翔天神。泰国阿瑜陀耶的法律蓝本是印度教的《摩奴法论》,从信仰佛教的孟人那里间接获得。关于《摩奴法论》的来源,印度教认为,梵天授法给摩奴,摩奴转授古代的博学之士。孟人接受后重编故事,以符合佛教教义[31]。佛教版的法论起源故事一直流传,曼谷王朝建立初期整编从阿瑜陀耶继承的法律,在新版的《三印法典》里对此仍有记载。故事讲述,佛陀时代,菩萨转世为国王。朝中国师帕塔拉古曼与法官摩奴三(Manusarn,即印度教版本的摩奴)乃梵神王婆罗默提瓦转世的后代,属于婆罗门种姓。摩奴三曾因断案不公遭受指责,故出家归隐,终修具五神通、八禅定,通晓民意。为使国王成为谨遵十王道的明君,摩奴三飞至宇宙边,背诵边墙上的巴利文《法论》,回来写成法论经书[32]。可见,无论是印度教法论来源故事中摩奴接受梵天旨意,从天而降传授《摩奴法论》,抑或佛教版故事中摩奴三作为色界梵天神的后代,飞到宇宙边带回《法论》,都表明法论具有超越须弥山的神圣地位,而摩奴或摩奴三则是法的使者。由于故事经久流传,中南半岛人对于摩奴三并不陌生,把他塑造为飞翔天神是可行的。至于天神手里“内部有十分浅淡的横线纹路”的器具,则是一部法典。古代中南半岛最常见的书籍是贝叶经,形状为长条矩形,内部有横线纹路,恰好与器具外观相符。摩奴三处于浮雕中轴的最高点,把法典置放于须弥山顶上,意在突出法的重要性。古高棉司法由婆罗门掌握。身为婆罗门的吴哥寺设计者提婆伽罗班智达在世时地位崇高,曾任三朝国师,走遍古高棉地区的宗教场所,代替国王献祭膜拜,死后更得到苏利耶跋摩二世的高度赞誉:“提婆伽罗班智达脚踩苏利耶跋摩二世的王冠”[33],记录在柏威夏寺的碑刻中。因此,鉴于设计者本人受到国王的敬重,即便想借浮雕突出自己或抬高婆罗门阶层的地位,也不会冒犯吴哥寺的主人苏利耶跋摩二世。更重要的是,苏利耶跋摩二世有能力、有抱负,需要借助婆罗门弘扬正法,宣扬自己是神化国王,为自己的过往正名,吴哥寺的建造就是明证;同时,他更需要依法治国,惩恶扬善,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而对秩序的感悟和追求,本身就隐含在吴哥寺面朝西、逆时针回廊的设计理念中。正是婆罗门的辅佐,促成苏利耶跋摩二世在位30余年间的国力强盛。因此,飞翔天神就是法的使者,在须弥山顶摆放法典,表明国王推崇法治,也暗指婆罗门受到国王的敬重。 四泰国对古高棉法王思想的汲取 吴哥王朝的神王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早期崇拜战神因陀罗和创造之神湿婆[34],苏利耶跋摩二世时,信仰保护神毗湿奴成为主流[35]。吴哥寺回廊浮雕反映出该时期的神王文化在表达国王是大神化身的基础上,还具有保护和弘扬正义的重要内涵。浮雕中轴线上,法的使者把法典放置在须弥山顶,象征苏利耶跋摩二世志在成为法王,所以毗湿奴神王文化含有鲜明的法王思想。苏利耶跋摩二世之前,毗湿奴信仰已经传入,众多那罗延造型艺术证明,其在位时毗湿奴信仰发展到顶峰,艺术作品蔚为壮观。但总体来说,吴哥推崇毗湿奴信仰的土壤并不深厚,宫廷信仰多数时期仍多以湿婆教为主。苏利耶跋摩二世之后的国王推崇大乘佛教,湿婆教也卷土重来,周达观游访当地时,南传佛教开始从底层渗入[36]。可见,毗湿奴法王理念在吴哥神王文化中孕育、成长,在当地并没有得到较好的继承和发扬。然而,从暹罗法律制度对古高棉的借鉴来看,毗湿奴法王理念的对外推广却有别开生面的景象。 素可泰法律制度发展落后,但有汲取古高棉法王思想的痕迹。素可泰在建立之前属于吴哥王朝的势力范围,吴哥早期崇拜的因陀罗神王文化对其产生影响。素可泰首任国王珀昆西因塔拉缇(年即位,卒年不详)的名号含义是“因陀罗—太阳”,是其盟友珀昆帕孟得到吴哥王朝的赐予转赠的,珀昆帕孟则统治毗邻的盛行崇拜毗湿奴化身罗摩的孟叻[37]。三世王兰甘亨时期(RamKhamhaeng,—9年),效仿孟叻崇拜罗摩,国王名字中有“罗摩”(Ram)为证[38]。由于南传佛教逐渐传播开来,后世国王改用与佛教有关的“法王”称号,导致泰国的法王思想主要体现为与佛教相关。虽然兰甘亨没有以法王为名号,但他在位时立下“兰甘亨石碑”,对关税、贸易、遗产、土地所有权等问题作出说明,体现了法的意识。六世王立泰(年即位,卒年不详)一生致力于弘扬佛教,即位前创作了被喻为第一部佛教教科书的《三界论》,在卷首提到著书“以释阿毗达摩和向母王说法”[39]。“阿毗达摩”即佛教大法、三藏中的论。立泰著书阐释大法,并提议母王“广纳通晓法的婆罗门修道者,予以崇高地位,作为法律顾问”[40],即位后号称“法王一世”。如果说兰甘亨时期统治者的法王思想还不甚强烈,与古高棉法王思想的渊源还有待更多的史料证明,到立泰时期则已很清晰。但总体说来,素可泰法律制度发展缓慢。泰国法学教授比里·格森萨(PreedeeKasemsup)认为,素可泰的法律是乡土法律,即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与错的辨别原则,在道德观念的基础上形成[41]。社会秩序乃至王权的稳定主要依靠道德教化维持,体现在礼俗中。泰北女权文化氛围浓厚,从妻居住、女性当家和女性同样有权继承家产的风俗则盛行至今[42]。在此文化氛围中,作为国王,获得母王或女王的支持极为关键,立泰著书为母说法,说明敬重母王,以传统礼俗为尊,这就是女权文化社会的反映,与尊礼尚法的古高棉法王思想的影响分不开。 阿瑜陀耶法制则有较大的发展,古高棉法王思想对之影响深刻。一世王乌通(—在位)的名号“颂迪帕拉玛缇波迪一世”含有“神王毗湿奴化身的罗摩”的意思,他借鉴吴哥的统治制度,颁布了证人法、拐带法、盗窃法、土地法、婚姻法等10部法令[43]。八世王戴莱罗迦纳时(—),暹罗法律制度的框架基本形成,沿袭至20世纪初。据史料记载,年,阿瑜陀耶派军攻克吴哥,掳掠回的大批婆罗门法师和官吏成为戴莱罗迦纳改革的主力。其政治制度借鉴吴哥,增补了几部重要法律如大刑法、叛乱刑法、萨迪纳土地制度比较法、宫廷法等[44],以保证国王的权威,加强政治统治。戴莱罗迦纳原本崇尚毗湿奴神王文化,其名号就是“三界之王的毗湿奴”之意,其身为太子之时统管的军事重镇彭世洛也意为“毗湿奴世界”。阿瑜陀耶统治者重用婆罗门,推崇法王理念。阿瑜陀耶建国时期,法律条文由婆罗门执笔制定,到了戴莱罗迦纳时期,法律制订、案件的审理和判决都由精通法论的婆罗门主持[45]。婆罗门对于古高棉法王思想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语言也是一个明证。阿瑜陀耶之前的法律条文中已有不少皇语,建国后皇语更加泛滥,而皇语多借自古高棉语,有好几百字吴哥时期的碑刻为证[46]。皇语是王权崇拜的一种体现,乌通在年出台的国家刑事法已明文规定要正确使用皇语[47]。擅长古高棉语的婆罗门从法律制定到执行上,确立了皇语的神圣地位。时至今日,皇语仍有严格的使用规范,成为泰语的一大特色。 泰国法制的发展反映出吴哥法王思想的影响不仅在空间上推广,还有历史的传承。吴哥势力范围所及,因距离权力中心的远近、自身内部条件和需求的不同,受到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从暹罗北部的素可泰和中部的阿瑜陀耶两地所受的影响来看,前者较弱,后者巨大。素可泰以降,佛教因统治者的大力扶持而迅速发展,但古高棉法王思想的影响至今犹在。曼谷王朝十任国王均以罗摩王自居,《罗摩衍那》为皇家寺庙玉佛寺回廊壁画的唯一题材,泰国公务徽章为毗湿奴的坐骑大鹏鸟,皇语的使用等等,都反映了泰国对古高棉法王思想的汲取和继承。吴哥法王思想的影响促成暹罗王权的巩固和发展,不仅形成一套皇家礼俗以烘托王威,保障国王神圣地位的法律也越来越健全。尊礼尚法的精神从吴哥王朝时代传承至今,促成泰民族王权崇拜特性的形成。年泰国改政体为君主立宪制,是尊礼尚法的民主革命结果。国王在宪法之下没有实权,但在礼俗中仍享有至高地位,其神圣性受到宪法的明文保护。 在造型艺术的表达上,吴哥寺尚法的创意设计在现当代泰国也留有痕迹。把崇尚之物置于中心或最高处膜拜,在中南半岛较为普遍。信仰南传佛教的柬埔寨国旗上的中心图案是吴哥寺,从法属柬埔寨保护国时期到现在的联合王国时期一直如此,但其本义是以伟大的文化遗产激起民族认同感,而非宣扬神王文化或法王理念。曼谷王朝为整顿僧纪而创立佛教法宗派的四世王蒙固(—年在位),被泰国人公认为一个具有十王道的法王[48],他在玉佛寺的中心增建吴哥寺模型,以示敬仰古高棉文化。如果说这个造型艺术还不够突出尚法精神的话,那当我们看到年建立的泰国民主纪念碑——高耸的圆顶堡垒状建筑之上,放置着高脚双层托盘,正中呈放一部矩形的、带着浅横线的传统泰式书本状宪法文书[49]——则能心领神会。 注释 [1]彭树智主编,肖宪、吴涛等著《泰国人》,三秦出版社,年,第87页。 [2]???????????????????????????????????????????????:O.SPrintingHouseCo.,Ltd.,?.52(〈泰〉玛达亚·英克纳律:《泰国历史》,曼谷:奥迪安士多出版社,年,第52页). [3]同上,第52-53页。 [4]年前的泰国称为暹罗。 [5]本文讨论的浮雕故事,笔者用“搅乳海”指称,其它的汉译名如“翻搅乳海”和“搅拌乳海”,笔者认为均值得商榷,留待日后另行撰文探讨。“搅乳海”故事讲道,天神和凶猛好斗的阿修罗为取得长生甘露而相约一同搅乳海。保护神毗湿奴拔取曼陀罗山为搅杵,蛇王(那珈)婆苏吉做搅绳缠绕其上,众阿修罗拽住蛇王的上半身,诸天神拉着其下半身,一起搅动乳海。毗湿奴化身巨龟,沉入海底顶住搅杵,以免搅穿大千世界。千年以后,长生甘露终现,毗湿奴又变身美女迷住阿修罗们,众天神得以独享甘露。 [6]李颖:《“翻搅乳海”:吴哥寺中的神与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2-3页。 [7]为行文简洁,若非特别强调,下文中的“吴哥寺的搅乳海浮雕”均简称为“浮雕”。 [8]那罗延(即毗湿奴)睡乳海时,肚脐眼长出带茎托着梵天神王的莲花,这个主题浮雕也常见于吴哥古迹。 [9]泰国、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的语言中,蟒蛇一词借自古印度的语言,叫“那珈”,发音大体相同。蛇王在泰语中叫phayanak。 [10]肘”是古印度建筑工程中常用的长度单位,一般指人体的肘关节至中指指端的距离,长度取决于房屋主人的手肘长度,此处肘的长度是苏利耶跋摩二世的肘长。转引自李颖《“翻搅乳海”:吴哥寺中的神与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第-页。 [11]相关论述详见吴圣杨《东南亚那珈信仰的起源与嬗变——语言民族学视角的分析》,《世界宗教研究》年第3期。 [12]?????????????????????????????????:???????????,.?.18(〈泰〉苏吉·翁特:《那伽来自哪里》,泰国珀斯特布出版社,年,第18页). [13]?????????????????????????????????????????????????????????????????????????????????????????????????????????????????19???????1??????????(〈泰〉唐旭阳、吴圣杨:《扶南建国传说的文化内涵探究》,《泰国东方艺术期刊》年第2期). [14]〈泰〉西萨甘·万立坡东:《泰国东北文明》,《文化艺术》特刊,年12月。转引自〈泰〉苏吉·翁特:《那伽来自哪里》,泰国珀斯特布出版社,年,第14页。 [15](元)周达观著,夏鼐校注《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年,第64页。 [16]〈澳〉A.L.巴沙姆主编,闵光沛等译《印度文化史》,商务印书馆,年,第页。 [17]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18]张晓华:《佛教文化传播论》,人民出版社,年,第39页。 [19]关于这件“器具”,《摩诃婆罗多》中的用词是yantra,金克木先生的中文译本译为“器具”。 [20]李颖:《“翻搅乳海”:吴哥寺中的神与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21]毗耶娑著,金克木、赵国华、席必庄译《摩诃婆罗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59页。 [22]转引自李颖《“翻搅乳海”:吴哥寺中的神与王》,第84页。 [23]李颖:《“翻搅乳海”:吴哥寺中的神与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80页。 [24]李颖:《“翻搅乳海”:吴哥寺中的神与王》,第83页。 [25]李颖:《“翻搅乳海”:吴哥寺中的神与王》,第84页。 [26]李颖:《“翻搅乳海”:吴哥寺中的神与王》,第页。 [27]16世纪后寺庙改名为“AngkorWat”,汉译为“吴哥窟”。 [28]《翻》认为,天空缥缈而不可捉摸,神所居住的天空之城没有确切的空间感,因陀罗扮演极点的角色,他飞跃须弥山,为天空设下一个最高点,众神及其居所才得以从无所依托的状态下解脱出来,宇宙空间秩序才得以建立。 [29]李颖:《“翻搅乳海”:吴哥寺中的神与王》,第页。 [30]李颖:《“翻搅乳海”:吴哥寺中的神与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96-97页。 [31]???????????????????????????????????????????????:???????,,?.87-88(〈泰〉萨翁·汶嚓楞威帕:《泰国法律史》,曼谷:文亚春有限公司,年,第87-88页). [32]??????????????????????????????????????????????:??????????????,,?.-(〈泰〉皇家学术院:《三印法典》(第一卷),曼谷:皇家学术院,年,第-页). [33]MadeleineGiteau??????.?.??????????????????????????????????????????????????:?????,,????64(〈泰〉玛德琳·吉托著,素帕迪·迪萨衮译《吴哥史》,曼谷:马蒂存出版社,年,第64页). [34]湿婆是印度教三大天神之一的创造和毁灭神,另外两尊是保护神毗湿奴和创造神梵天。 [35]??????????????????????????????????????????????????????????????????:???????????,,?.(〈泰〉吉·普密萨:《阿瑜陀耶史前湄南河流域的社会》,发辽干出版公司,年,第页). [36]李颖:《“翻搅乳海”:吴哥寺中的神与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37]??????????????????????????????????????????????????????????????????:???????????,,?.(〈泰〉吉·普密萨:《阿瑜陀耶史前湄南河流域的社会》,发辽干出版公司,年,第页). [38]同上,第页。 [39]???????????????????????????????????????????????????????????????????????:??????????????,,?.4.(〈泰〉皇家学术院:《素可泰文学词典:三界论》,曼谷:皇家学术院,年,第4页). [40]同上,第页。 [41]???????????????????????????????????????????????:???????,,?.64(〈泰〉萨翁·汶嚓楞威帕:《泰国法律史》,曼谷:文亚春有限公司,年,第64页). [42]关于泰北女权文化的研究,详见吴圣杨《八百媳妇遗风余韵——语言民族学视角的泰国女权文化探幽》,《南洋问题研究》年第2期。 [43]???????????????????????????????????????????????:O.SPrintingHouseCo.,Ltd.,?.54-55(〈泰〉玛达亚·英克纳律:《泰国历史》,曼谷:奥迪安士多出版社,年,第54-55页). [44]同上,第63页。 [45]同上,第55、65页。 [46]??????????????????????????????????????????????????????????????????:???????????,,?.70(〈泰〉吉·普密萨:《阿瑜陀耶史前湄南河流域的社会》,发辽干出版公司,年,第70页). [47]同上,第63页。 [48]???????????????????????????????????????????????????????????????????????????????????:?????????,.?.(〈泰〉帕沙甘·翁达万:《泰国历史:从背井离乡到年革命》,曼谷:吉普西古鲁,年,第页). [49]以托盘承托重要物件的习惯在泰国、老挝和柬埔寨非常普遍,常见托盘边沿制作成莲花花瓣状。传统泰式书本,是用鹊肾树皮做成的纸折叠而成,一般比贝叶经书短而宽。 原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年第2期 本文转载自东南亚研究公众平台 赞赏 长按白癜风治疗方法北京中科医院是治啥的
|
当前位置: 金塔县 >吴圣杨泰国法王思想探源兼评
时间:2018/9/20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金塔汽修中专荣获全国农村优秀学习型部
- 下一篇文章: 董卿的朗读者精华100句,只读一遍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