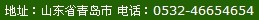|
白癜风专家郑华国 https://m-mip.39.net/disease/mipso_5464402.html摘要:马鬃山是河西走廊西段的一座山脉,也是进入蒙古高原和新疆地区的一道门户。20世纪上半叶围绕马鬃山及周边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族群流动,在当地引发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影响了河西走廊及周边地区的社会平衡。苏联的地缘政治影响波及中国西北边疆,使马鬃山呈现出一定的边疆性特征。同时天山一带的哈萨克民众与新疆军阀之间的冲突,也与苏联有着潜在的关联。在这种情形之下,苏联的地缘政治影响在传输过程中逐渐进入河西走廊的西段,使马鬃山成为河西走廊周边社会能量的传导中心。周边不同族群通过马鬃山进入走廊内部,对于20世纪河西走廊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塑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族群流动;社会平衡;多民族分布格局;河西走廊;马鬃山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河西走廊民族语言的跨学科研究”(18ZDA)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李建宗,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社会、族群关系、民俗学。历史上的边疆与河西走廊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要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思考。正如袁剑所说,“我们需要重新理解作为各部分的边疆空间以及作为整体的边疆空间在整个中国空间中的历史与结构意义”[1]。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河西走廊呈现出部分边疆性特征,到年之后,这一区域成为中国边疆空间的组成部分。黄达远指出:“从学理上看‘区域中国’,避免了传统‘边疆观’的窘境,可以在区域的不同的时空面向下,讨论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形成‘从边疆看边疆’‘从边疆看中心’‘从中心看边疆’,并从这几个层面的连续性、交互性中理解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更为深刻地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思考中国和边疆的历史”[2]。历史上的河西走廊,不同历史时期周边地区的动荡和变革都会波及到当地并影响走廊内部的族群分布状况和社会文化结构。河西走廊的意义是动态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对周边地区有着不同的作用,这也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特征。河西走廊地处与之相连的几个大文化区域之间,反而呈现出一些“中心”的特征。河西走廊既是周边文化区域变迁的“晴雨表”,又是缓解周边地区社会危机的“安全阀”[3]。王铭铭在论述“三圈说”时指出:“‘三圈说’之提出,既是为了理解中国史的空间架构,又是为了对这些不同的角度有所综合,为了在综合的基础上广义地理解作为一个研究地区的中国的多元一体格局”[4]。关于历史上河西走廊的认识,不仅首先要跳出河西走廊自身,充分考虑河西走廊的周边地区,还要涉及与之相关的“外围”部分,这就是“三圈说”在边疆研究中的意义。在特定历史时期,从河西走廊可以发现周边地区的社会状况,换个角度说,只有从周边地区切入,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河西走廊。马鬃山地处河西走廊的西段,是走廊北山系列中最西边的一座山脉。马鬃山口岸位于甘肃省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镇,是甘肃省境内唯一的边境口岸。尽管马鬃山口岸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但马鬃山仍属边疆区域。历史上河西走廊的畜牧业占有相当的比重,主要有山地游牧与戈壁畜牧两种形态,其中山地游牧包括南山游牧带(祁连山游牧带)和北山游牧圈。与河西走廊南面的祁连山游牧带相比较,北山游牧圈的草场质量不太好,游牧社会的规模不大。然而,20世纪上半叶围绕马鬃山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事件,它们既是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反映,也是河西走廊周边游牧社会状况的部分呈现。可以说,近代以来马鬃山游牧社会的变迁对河西走廊的民族分布格局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一、河西走廊周边社会问题与马鬃山的族群流动《马鬃山调查报告书》指出,马鬃山“西邻新疆,北依外蒙,东拱宁夏,南与酒泉玉门安西诸县齿错相接,周约二千余里”[5](P.1)。马鬃山横亘于河西走廊的西北边缘,地处库伦草原、天山山脉、阿拉善古高原、柴达木盆地之间。历史上在马鬃山兴起过一定规模的游牧社会,也出现过一些零星的农业生产。由于马鬃山具有一定的游牧生存资源,能够容纳部分游牧族群,每当周边游牧社会的部分族群出现生存困境时,便会进入马鬃山寻求生存资源。雍正元年(年)罗布藏丹津事件之后,清政府在青海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根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查明青海蒙古乃二十九家,即分为二十九旗”[6](P.)。在青海蒙古二十九旗中,柴达木盆地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南文渊指出:“年编旗时,柴达木地区蒙古编为八旗:西前旗、西后旗、北左末旗、北左旗、北右末旗、西右后旗、西左后旗、西右中旗”[7](P.-)。《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志》指出:“肃北蒙古族的渊源,大部分是在清朝中后期从青海厄鲁特蒙古中的和硕特部北左翼右旗,及北右翼末旗等迁徙发展而来的。”①相应地,部分青海厄鲁特和硕特部蒙古民众也进入马鬃山。从20世纪初开始,新疆土尔扈特部蒙古民众先后进入马鬃山。光绪二十七年(年),“又有新疆土尔扈特蒙古二十余幕,逃牧于明水等地,安西州委巴图索尔为头人率领之”[5](P.3)。这20多户来自新疆的土尔扈特部蒙古民众“因不堪头目的剥削”[8],逃牧于马鬃山,是20世纪首次进入当地的土尔扈特部蒙古民众。年,“新疆和硕特部牧民25户进入马鬃山游牧”;年,新疆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部蒙古牧民又有36户进入马鬃山放牧[9](P.16)。20世纪初期,新疆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蒙古民众离开自己长期游牧的草场,一路向东进入马鬃山,一方面为生存所迫,另一方面是“带动效应”。马鬃山地处天山山脉东端,属于天山余脉。20世纪上半叶,新疆天山游牧带以及周边游牧区域内部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部分游牧族群迫于生计而开始流动,企图寻找一块可供自己生存的游牧栖居地。马鬃山与阿拉善高原之间具有地缘关系,当时阿拉善高原的部分蒙古民众也进入马鬃山游牧,如20世纪30年代“来自阿拉善王旗者约六七十幕”[5](P.9)。清末民初的马鬃山成为库伦地区喀尔喀部蒙古民众逃避社会灾难的一个“基地”。20世纪上半叶,农耕地区的民众因逃避债务进行流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也出现于游牧社会。年,库伦地区30多户喀尔喀部蒙古民众因债务危机进入马鬃山,史载“当光绪二十七年时,有外蒙喀尔喀札萨克图汗加比公旗加仑王旗等处蒙民三十余幕,因负汉商大盛魁债甚重,相率逃入山中,牧于墩墩山一带”[5](P.3)。从此,马鬃山对库伦地区的蒙古民众产生了吸引力,他们不断进入马鬃山放牧。随着库伦地区喀尔喀部蒙古民众在马鬃山频繁出没,库伦当局高度警惕,多次组织遣返马鬃山的蒙古民众,然而很多被遣返回去的蒙古民众又设法逃回马鬃山,有些甚至是“两进两出”。史载“光绪二十九年,加比公旗曾派员来山召回旗民十余幕,伊里克三星保等均返旗。迨宣统元年,伊里克三星保又二次逃入山中”[5](P.4),“民国八年,加比公旗复派员来山召回本旗蒙民十余幕”[5](P.4)。年,丹毕坚赞(又译为淡必加餐、丹宾坚赞等)遇刺之后,马鬃山大量喀尔喀部蒙古民众被遣返到库伦地区,然而没过多久,库伦地区的部分蒙古民众再次进入马鬃山。史载“民国十三年春,自外蒙逃来蒙民六十余幕。先是淡必加餐既死,山中喀尔喀蒙人悉为库伦方面召回,至是外蒙新党得势,反对派之蒙人,遂相率入山趋避。明年,伊里克三星保等,亦偕十余幕三次来山。合计先后至山游牧者,已达百余幕”[5](P.8)。随着库伦当局内部政治形势的变化,大量喀尔喀部蒙古民众向马鬃山加速流动。“初,外蒙政权既握于新党之手,反对派之蒙人,多相率逃入马鬃山,为外蒙新党所嫉视”[5](P.10),关于这一点,Y·C.铁穆尔和图雅曾有所论述[10](P.48)。丹毕坚赞及随从作为库伦当局的反对者进入马鬃山,引发了喀尔喀部蒙古民众流动的第一次高潮,后面又有大量库伦当局的反对派人士相继进入马鬃山。自年以来,库伦当局出现了“亲苏”倾向,范丽君指出:“年7月10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11月25日建立蒙古人民革命政权,新政府与苏联签订《蒙苏修好条约》”[11]。库伦当局政治局势的变化影响了部分蒙古民众的切身利益,随后激起了他们对库伦当局的抵制与反抗。为了逃避库伦当权者的压制与迫害,一些库伦当局的反对者向马鬃山流动。马鬃山对库伦地区的部分蒙古民众产生了“向心力”,同时也意味着这些蒙古民众对库伦地区具有强烈的“离心力”。在这种情况下,库伦当局总是设法阻止当地人群向马鬃山流动并多次在马鬃山进行遣返活动,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和恐怖手段。20世纪20年代后期,新疆天山游牧带部分哈萨克民众已经到过马鬃山。根据马铃梆的记载,哈萨克民众首次于年进入马鬃山,“民国十七年,三星保等移牧山南桥子地方。自新疆逃来哈萨克四十余幕(哈人入甘之始)”[12](P.)。郭曙南指出,年,新疆天山游牧带部分哈萨克民众因不满当时的军阀统治,由爱毒(阿都)巴依率领房子一百二十三顶,人口约三四千人,牲畜约万余,沿新绥公路进入甘边马鬃山,转而进入玉门县祁连山下鱼儿洪(鱼儿红)游牧[13]。关于哈萨克民众进入马鬃山的时间,还有不同的说法。《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概况》指出,年1月,新疆巴里坤一带的哈萨克民众因逃避捐税,惧怕谣言,在部落头目阿都巴依的带领下赶着数千牲畜来到马鬃山,共户,人,这是哈萨克民众大规模进入甘之始。同年6月到鱼儿红、托赖等地游牧[14](P.18)。《新疆哈萨克族迁徙史》指出:“年至年间,哈萨克族大批东迁甘肃境内留牧,先后四批移至河西走廊,计约多户2万多人。一部分游牧于酒泉之南的祁连山、托赖、鱼儿浑等地。一部分进入青海,游牧于都兰、格尔木、马海、茫崖等地。后来,这两部分牧民中又分出一些移牧于安南坝、太吉淖尔、哈尔腾、赛尔腾和海子一带。”[15](P.79)20世纪30年代,哈萨克民众在“东迁”过程中首先进入河西走廊,然后部分进入柴达木盆地及青藏高原其他地区。民国时期大量土地集中到少部分富人手中,一些穷困的汉族民众不得不到处寻求生存资源。农耕地区的部分汉族民众进入周边游牧地区进行垦荒种地,在河西走廊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来自周边农耕地区的瓜州、玉门、敦煌一带的部分汉族民众,为了生存进入马鬃山,从事农耕或者游牧生产活动,“马鬃山幅员辽阔,水草丰美,颇多垦牧咸宜之区。自清末以来,东之额济纳,西之土尔扈特,北之喀尔喀,及安西一带之汉民,多相率徙牧其他”[5](P.20)。20世纪上半叶,在全国“禁烟”的社会大背景下,一些边远地区出现了鸦片种植与销售的产业链条,西北地区也不例外。特别是一些“流民”性质的汉族民众铤而走险,在山区偷种鸦片谋生,“民国七年,适禁烟令严,河西汉民二百余人,逃至山中伊克高鲁地方偷种鸦片”[12](P.)。随着马鬃山游牧规模的增大,当地的畜牧及狩猎产品引起附近汉族商人的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jintazx.com/jtyy/6817.html |
当前位置: 金塔县 >李建宗丨族群流动与社会平衡20世纪上半叶
时间:2020/10/3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台风委员会第51次届会开幕台风的名字谁说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