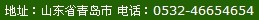|
忆起《三笑》这部香港戏曲电影,简直有种与生俱长的感觉。那时我还住在南昌的金塔街,念着小学。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南昌公共汽车交通公司,它的门前经常贴着电影海报。有一天我看到了硕大的几个彩墨毛笔字: 香港彩色故事片 三笑 三笑,这个电影常听外婆和妈妈提到,每次都眉飞色舞。我当即激动地一路跑回家报告。那时我们和外婆家比邻而居,外婆这人有着极品的浪漫,虽然她不过是个酱油厂拉板车的临时工,近乎庸保,目不识丁。每天一早,便须和我妈妈两个推着板车奔跑于南昌的大街小巷;可她骨子里的小资气息之浓厚,可以用来泡茶。也许我用词不当,她的所谓小资,并非如我的同学方子郊所言,坐在星巴克的咖啡屋里,忧郁地呷着咖啡那类。她的表现是那样的独特:不管多忙,只要路过电影院,必定停车看那花花绿绿的海报,见到有穿戏曲服装的,则会着急地对我妈妈说:“赶快去买票,送完下一趟,去看电影。”接着这母女俩干劲冲天,拖着空板车往电影院狂奔,也顾不得回家换件稍微体面点的衣服。她们将板车寄存在电影院门口,小跑着进去,引来路人惊呼:“乡下人进城啰!” 那个年代的戏剧片产量很不少,一年必有几部。而故事也大多不过是落难公子中状元,最后又赢得美人归之类,总之离了困顿、误会、悲痛、爱情和团圆,便没法演。虽然老套,外婆却看得津津有味。她根本一个字不识,唱词是几乎不知道的。统计一下,每部片子她必看数遍,象越剧大片《红楼梦》,竟有三十遍之多。然而在她的圈子里,并不是冠军,附近有个单身老妪以三十三遍的记录夺得金牌。我还记得彼刻,看见外婆盯着那个春秋甚高,却穿着呢子大衣,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同庚姐妹,一脸不服。可惜那时并没有所谓影碟,否则,外婆定会熬夜加班,接连看完五遍才罢休。当然,即便如此,她也不是没做过适当努力,她曾经浼求别人,能否帮忙雇个放电影的,自己出钱来家中的院子里放那么一两场《红楼梦》,可最终因为外公的干涉,提议搁置了。如此的迷恋戏剧,或许在今天真正的小资看来,非但算不得同类,反而是十足的腐臭。可是小资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就在前两天,还有人说我小资呢。天可怜见,我一不吃西餐,二不喝咖啡,衣服晦暗,头发蓬乱。跟小资这概念完全云泥相隔。最后她说出的理由竟是:你这厮经常读那劳什子秦汉竹简,从坟墓里挖出来的,跟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审美趣味天差地远,不算小资算什么?好吧,愈加之罪,何患无辞。既然小资的概念是如此可以因地制宜,见风使舵,那么我将它扣在我那当年五十多岁的外婆头上,大概也算不得不可以吧。 总算要扯到正题了。话说我一回去,告诉外婆有《三笑》,她的眼睛刹那间亮得吓人。快去买票。她边说着已经掏腰包,这部片子好看,我才看了十一遍,比老妖精少多了。老妖精就是前面提到夺得《红楼梦》观看金牌的那位。她把钱递给我。自然晚上我是要一同去的,叫我去买票,就不能没我的份,这是规矩。可是那是场什么电影呢?我真的糊涂了。我现在唯一记得的是,那次买了好多票,晚上我们几乎倾巢出动,我外公、舅舅、姨,一大堆。回来的时候我二舅舅还在哼哼:“尊一声二奶奶,听我表一表。华安原是块好材料。从小宝护金,长大金护宝,屈膝为奴这是第一遭。我的好二奶奶呀,你好心成全有好报。”我却只顾去菜橱里用手指钳剥皮鱼制成的干鱼块吃。他们很欢乐,热烈讨论,根本不管我。我吃了好多块。就在那个星光摇曳的晚上,我养成了伴随我一生的习惯:看电视的间隙,跑到客厅里用手指钳桌上的干鱼吃,非常快意。这能不能通过心理学得到什么解释? 我仍然愿意回忆那场《三笑》带给我的记忆,但是好像除了唐寅出场的那句唱词“唐寅脱去解元巾,纸扇轻摇佛殿临”,就什么都不记得了,那还是因为我刚自学了初中语文课本上《儒林外史》的“范进中举”那段,知道解元是举人中最牛逼的,谁能不知道各行各业中最牛逼的呢?我甚至连剧中秋香的扮演者大美女陈思思都没留下什么印象,这简直是他妈的唐突佳人,该死之极。风华绝代的美女,倒不如那几块咸鱼干能给我更深的记忆,看来我的劳什子情商真的不高。当然,我也可以用“我那时还小啊”这句混帐话搪塞过去,但是想想,人家刘彻呢?人家才七岁,就知道要用金屋贮藏美女,以便将来好生地享用了。我纵然搞不到金屋,但脑子里做个白日梦以意淫的念头,总不该没有啊! 一直等到我工作后,看到音像店《三笑》的影碟,想起年少时他们的痴迷,就笑着买了回来。一看之下不由惊叹,天啊!香港竟拍过这么好看有品位的片子么?我在念大学时,看过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那他妈的实在是太无聊了,无聊加黄色。而这个《三笑》,普通话的对白里穿插的那大段的曲子,从名称上看,是多么的雅致啊。似乎都是悦耳的苏杭小调,什么《茉莉花》、《湘江浪》、《山歌调》,特别是填的歌词都还算精巧,这在看过大陆近年来粗鄙不堪的电视剧歌词之后,感觉尤其清新。其实我对大陆文化界狂妄自大的习气早就感到可笑而鄙薄了,他们称呼香港为文化沙漠,可是我发现有些香港作家的语言驾驭能力,完全超过很多自以为是的大陆作家。前年我偶然读了几本通俗作家李碧华的小说,骇怪的是有一篇中某句话太古雅,竟至让我读不懂;而相比大陆,却是连魏叉叉那样的半文盲都敢于号称古汉语功底深厚,自封大师的。再说那个我听了无数遍的《帝女花·香夭》吧,里面那个胜国驸马的唱词:“泉台上再设新房,地府阴司里再觅那平阳门巷。”开始看到“平阳门巷”这四个字我也一愣,后来想起汉武帝的姐姐阳信长公主,因为嫁了平阳侯曹寿,又号平阳公主(武帝微服出宫时,常自称平阳侯,可见平阳侯当时的地位)。这才突然明白。 又扯远了,我要说的是,《三笑》之所以让我这样不厌其烦地看,曲调和唱词的优美,固然是个重要原因。但里面人物装束的精美,色彩的典丽,也是颇为悦目的。尤其是演员的选择,那唐寅的风神俊朗,虽然是女性反串,但丝毫没有带给我看电影《红楼梦》时,夏菁反串贾宝玉那样的厌恶。还有那致仕宰相的二个活宝儿子,一胖一瘦,表情滑稽夸张,唱词也相应的给予鄙俗而逗笑。真是从演员到作词,都善于择人。再要提到的,就是秋香的扮演者陈思思了,这会她的魅力比咸鱼干可大得多。如果影片的质量够清晰的话,我一定会将她的姿容拷下放在电脑桌面上的。她的美丽不好描述,我不能象林纾写文言小说那样滥用几个“长眉入鬓”、“丰姿天然”陈腐的词来打发,但我也确想不出更好的词汇。有些女人走近了才知道她的美貌。那样也好描述,只要实在地写下自己的感受就行。然而陈思思却活动在几十年前的屏幕里,那么远,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你叫我怎么办? 的外婆已经去世了十年,活了八十多岁。她死前的近二十年间,早就转变了人生乐趣。她的小资情调一扫而光,灵魂皈依了上帝,每周除了去一次教堂,便是躲在房间里读竖版的《圣经》。灵魂被拯救的迫切何其重要,几十年来才子佳人的古典戏剧文化,没有赋予她丝毫认识汉字的欲望,反是靠着那异族异国的上帝,她读懂了竖版繁体字的《圣经》。我以前在课堂上讲《古代汉语》的时候,由于习惯,总是写繁体字,有一次终于有个学生嚷道:“那是个什么字?”我只好羞涩地擦去了,换写一个简体的补上。我想我那时是不是应该给他们讲讲外婆的故事呢?只是,《圣经》也早就有简体字本了,为什么我外婆要读繁体字本?难道她潜意识里,就觉得读繁体才算有文化,才有资格做个中西文化的交流使者?可惜已经无从询问。 最近我们上线了《梁惠王带你读古诗词》线上课程,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学习体验,也鼓励大家认真听课、一起学习,我们试着开发了“梁惠王带你读古诗词日签打卡”小程序,长摁上图识别
|
当前位置: 金塔县 >香港电影三笑和我的外婆
时间:2021/6/6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太牛了萧山这些让世界震惊的绝活儿,你见
- 下一篇文章: 一周要闻回顾3月9日至3月15日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